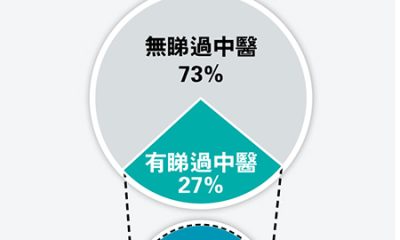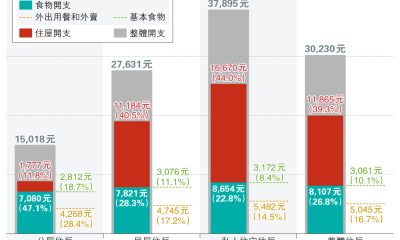觀點
烈顯倫:宣布性的裁決——法治抑或「法官之治」?警員有人權嗎?

【明報文章】普通法的一個重要原則是,法院行事從來不會是徒勞的——命令就是命令;當頒布了一個命令,隨之而來的必須是有效行動,裁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它不能消解成為文字的雲團。這一簡單原則卻經常為高等法院所誤解、忽視,甚至徹底違背(downright flouted)。
以2020年6月於高院一併審理的5宗案件為例,判辭於2020年11月19日頒布(HCAL 1747, 1753, 2671, 2703及2915/2019)。這些是要求啟動司法覆核程序的申請,警務處長於所有案件中被列為假定答辯人;而在最後一宗,律政司長被增添為假定答辯人。他們向高院尋求許可,以提出兩個問題:(1)警隊特別隊伍所穿著的新防護服裝,是否足以令人識別參與防暴行動的個別警員,而若不能夠的話會有何後果;(2)儘管處理對警察投訴的法定安排已載於法規裏,並已執行相當長時間,但其是否「違憲」?
司法覆核申請人的指控
申請人希望提出的指控是,上述兩個情况的安排皆違反了《香港人權法案》第3條(BOR3)。
有關訴訟源於2019年6月12日的事件。當時一大群不受控的暴徒(unruly mob)於立法會大樓外聚集,要脅打破屏障及衝入會議廳以中止程序——其時立法會正開會辯論有關《逃犯條例》的修訂。警方需要用胡椒噴劑和橡膠子彈去應對情况。
自此,街頭示威愈趨暴力,幾乎每日都有廣泛的公共設施和私營公司遭破壞的事件。警隊自身也成為攻擊目標;僅靠穿著制服的警員已不可能維持治安,故需動員特別隊伍,配以阻燃保護裝備、護肘、護膝、強化頭盔等。
特別警員隊伍之識別
由此引入一個新的識別機制,它有兩個目的:更好地安排警隊不同隊伍的工作,及同時在公眾投訴警方時可以識別個別警員。這採取了所謂的「藍卡」形式:一些放置在塑膠套裏的硬卡片,載有足以識別有關隊伍的信息,例如標示「C T3 Coy 2ic」,代表「Central District Tier 3 Company, second-in-charge」(中區第三梯隊副指揮官)。而在警員所戴頭盔的背後會有一個英文字母,標示該隊伍中的個別警員。此外,還有一支總部外勤行動支援隊,負責管理隊伍呼號(call-signs)、分配予個別警員的英文字母及其姓名、隊伍識別編號和職級的每日紀錄。如此可以在必要時查找到個別警員。
以上所述,是該5宗案件中毫無爭議的事實。
法官的態度
周家明法官是這樣介紹此事:「法庭裏有5份司法覆核申請。每一宗所提出的問題是,香港警務處人員在執行跟近期公共秩序事件相關的非秘密職務時……是否需要展示其獨有的識別編號……或其他獨特的識別編號或標記。」法官所指的「非秘密職務」,是由警方特別隊伍執行、代號為「踏浪者」的防暴行動。
他對有關問題的回答是「Yes」。他的結論是:有這樣的「需要」,而這一「需要」沒有得到充分滿足,因此違反了BOR3。
他相應地發表如下宣言(在66頁判辭的結尾):「警務處長沒有建立和維持一個有效機制,以確保每一名調動去執行『踏浪者』之非秘密職務的警員,均佩戴及顯眼地展示該警員獨有的識別編號或標記,是違反了香港人權法案第3條。」
即使不看BOR3,人們都可以見到此裁決有極其錯誤(radically wrong)之處。
根據這個宣布,警務處長該做些什麼呢?這類實務是需要法官干涉的嗎?「顯眼地」展示識別編號或標記,是什麼意思?有關機制在哪些方面有不足?若藍卡識別機制及其他措施不夠「有效」,那什麼才構成更好的機制呢?司法機構根據什麼準則判定「有效性」?警務處長如何知道識別機制的變更,是否滿足法官的要求?
法官是從歐洲人權法學的視角看待這些事情,而非運用簡單、實際的一般常識去處理問題。
可以看出,該宣布不過是一紙空文(a puff of hot air),沒有也不可能產生有效的實際結果。但當人們將注意力轉向法官該項宣布的法律根據,即違反BOR3,人們簡直是大吃一驚。該條文是這樣說的:第3條「不得施以酷刑或不人道處遇亦不得未經同意而施以試驗」:「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非經本人自願同意,尤不得對任何人作醫學或科學試驗。」僅此而已。
此條文沒有含糊之處,它處理的是當權者或政權所實施之極端不人道或侮辱行為。此處陳述之權利是絕對的,即是說無論發生何事,都必須以法律保護人們免於遭受這類行為。其含義來自有關文字本身。
BOR3絕對禁止極端、系統性的虐待,例如故意造成劇痛、故意損害人的境况(human condition)等。此條文怎麼可能適用於警務處長用以識別參與「踏浪者」行動之警員的機制?法官的宣布實在太怪誕(bizarre)。
調查投訴的制度
轉向該案的另一部分——調查對警察投訴的現行制度。有關事實同樣是毫無爭議的。
法官在其判辭一開始(段16)表示,申請人在啟動他們的訴訟時,以不同方式對個別警員提出「虐待」(ill-treatment)的指控;但他作為法官,裁定司法覆核不適合用作解決「主要事實的重大爭議(substantial disputes of primary facts)」。他只能夠把所提出的問題,作為原則問題去處理。因此於判辭第46至64段,法官詳述「處理對警員投訴的兩層機制」。
首先,是由一名高級警司領導的投訴警察課(CAPO),「大多數CAPO人員都接受過訓練,從中他們得到必需的調查技巧和能力。他們具有經驗處理一般的警務調查,以至是對警員投訴的調查」(段50)。
監督CAPO工作的是一個法定機構,即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監警會)。如法官所描述,監警會乃「一個獨立機構,既不是香港政府的僕人(servant),也非其代理人」;其成員「來自廣泛社會,包括法律、醫療、保健、教育、社福、通訊和商界,以及立法會議員」(段58)。監警會有廣泛權力,並設立了「觀察員計劃」,其成員可在突擊或預先安排下出席與CAPO調查有關之面談,及觀察蒐集證據的情况(段62)。
表面上,這種安排看來綽綽有餘。在判辭的某一階段,法官本人似乎也如此認為,因為他在第45段說:「儘管李先生(總督察)以雙重識別機制作標籤,去形容CAPO為識別被投訴警員而採取的方法及查詢,但似乎對我來說,那些不外乎是人們合理預期的、任何負責調查對警員投訴的認真機構所採用或執行的方法及查詢。」
法官的宣布
那麼,法官是如何就這個問題發表如下宣布:「根據香港人權法案第3條,香港特區政府有責任設立及維持一個獨立機制,能夠對警員涉嫌違反香港人權法案第3條之虐待行為的投訴,開展有效調查。而現行包括投訴警察課、並由監警會監察的投訴機制,不足以履行這個責任。」在這裏,讀者進入了魔術師的世界(illusionist’s world),當中黑可以變成白、怪物變成天使。
如前所述,BOR3絕對禁止酷刑和不人道或侮辱人格的對待。有人可能會問,這與處理對警員投訴的安排有何關係呢?警務處長是否設立了酷刑室去審問投訴人?
其答案——若這是正確用詞的話——在於由法官所稱的「史特拉斯堡法學」(Strasbourg jurisprudence)所產生的晦澀邏輯。但為何法官認為首先有必要訴諸史特拉斯堡法學,是一個謎,因為BOR3乃香港法規裏的條款,而其措辭並無含糊之處。
史特拉斯堡法學
儘管如此,法官表示《歐洲人權公約》第3條與BOR3是「實質上」(materially)一樣(段68)。但事實並非這樣。
如法官引述的Bouyid v Belgium(2016年)一案所解釋:「任何對人類尊嚴(human dignity)的干涉,都觸及《公約》之本質……基於此原因,執法人員對個人的任何貶低人類尊嚴之行為,皆構成違反《公約》第3條。這尤其適用於當他們對個人使用武力,而後者行為並沒有導致絕對必要的情况。」
BOR3並無表示它提供對「人類尊嚴」的保護——這是一個比保護免遭酷刑等遠為虛幻(illusive)的概念。認為BOR3保護「人類尊嚴」,是對該條款的輕視。採用這種解釋,就會失去字詞的清晰度,其堅硬邊沿就會變鈍。在史特拉斯堡法學之影響下,它們滑入了黑可以變成白的灰色地帶,黑夜與白晝的區別變得模糊。
此外,可以看出,Bouyid v Belgium案是關於一宗實際的警方虐待事件;比利時處理投訴的安排,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被裁判。但如上述,周家明法官在由他審理的這組案件中,明確排除了判斷申請人關於虐待投訴之真實性的任何嘗試。他說這在司法覆核程序當中並不合適,而申請人應透過民事訴訟尋求對損害的賠償。因此在他席前的整個聽證中,虐待的指控仍停留在指控,僅此而已。
或許是被史特拉斯堡法學弄糊塗了,法官正是在這裏完全茫然失措(lost the plot)。在提到不適宜裁定申請人所提出對警方虐待的指控之後,他表示(段77):「惟顯而易見的是有許多可爭辯的聲稱(arguable claims),是關於警員使用非必要或過度武力,或施以虐待的情况;倘證明屬實,或構成違反BOR3,從而觸發了政府方面的積極調查責任。」
「可爭辯的聲稱」?
應用法官的邏輯,僅僅的一個虐待指控變成「可爭辯的聲稱」。正如BOR3裏免遭酷刑等的保護,滑向了對「人類尊嚴」的保護。當透過歐洲法學視角審視在香港的人權時,就會發生如此情况。
法官引述大量有關保護個人人權的歐洲案例,但忘記了警員同樣有人權。兩層機制向公眾提供了投訴警方的途徑,惟也保護警方免受沒有事實根據或惡意的投訴。若「人類尊嚴」是個問題,那在這方面,警方如同投訴人一樣有權受保護。
於部分歐洲案例中,發現到有警員的虐待行為;在這裏則沒有。
法官席前的唯一問題是,處理對警方投訴的安排是否違反了BOR3。法官引述大量史特拉斯堡法院和其他海外機構的聲明,並從中得出如此觀點:「觸發了政府方面的積極調查責任」。
人們會想問:那又如何?兩層機制之整體目的,無疑正是為了履行「積極調查責任」。為什麼需要艱深字詞和海外案例來言說顯而易見的事呢?但法官卻由此做出了泰山般的跳躍(a Tarzan leap),發表他的宣言。這是一種原始權力的宣示(assertion of raw power),當中沒有邏輯。
總結
法治需要紀律(discipline)。倘人權法案或其他法規裏的簡單字詞沒有被賦予簡單含義,及法官被允許擴展其含義以符合所期望的社會結果,那就不再是法治。若字詞的含義如此虛幻,一般公民又怎麼遵守法律呢?這就變成「法官之治」(rule by judges)—— 一種變相的暴政(a form of tyranny in disguise)。
法官在此組案件發表了兩個空洞的宣布;66頁費解的文字,無論怎麼精通英語的人都不能夠理解。這就是施行司法的「透明」(transparency)嗎?
諷刺的是,儘管理論上申請人勝訴,但他們在過程中一無所獲。再一次,人權產業(human rights industry)成為真正贏家。
(編者按:原文為英文,由本報翻譯成中文)
作者烈顯倫(Henry Litton)是終審法院前常任及非常任法官
■稿例
1.論壇版為公開園地,歡迎投稿。論壇版文章以2300字為限。讀者來函請電郵至[email protected],傳真﹕2898 3783。
2.本報編輯基於篇幅所限,保留文章刪節權,惟以力求保持文章主要論點及立場為原則﹔如不欲文章被刪節,請註明。
3.來稿請附上作者真實姓名及聯絡方法(可用筆名發表),請勿一稿兩投﹔若不適用,恕不另行通知,除附回郵資者外,本報將不予退稿。
4. 投稿者注意:當文章被刊登後,本報即擁有該文章的本地獨家中文出版權,本報權利並包括轉載被刊登的投稿文章於本地及海外媒體(包括電子媒體,如互聯網站等)。此外,本報有權將該文章的複印許可使用權授予有關的複印授權公司及組織。本報上述權利絕不影響投稿者的版權及其權利利益。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烈顯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