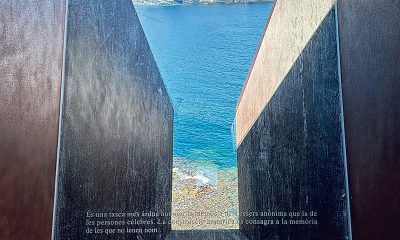副刊
{黑臉疲勞達人}余日東 黑臉琵鷺守護者 盼小伙伴毋須搬家

【明報專訊】睇雀睇了30多年的余日東(東爺),臉早被太陽曬黑,接任環保團體香港觀鳥會(鳥會)總監後,除了黑臉還多了疲勞,愈來愈像他保育的候鳥「黑臉琵鷺」。在上周日世界候鳥日前幾天,記者跟東爺到米埔實地睇雀,預想北部都會區(北都)發展影響。東爺小心喚團友勿驚擾雀鳥,謹慎籲最好不要問太多。要到了觀鳥亭,拿起望遠鏡,他才放下警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隻。」魚塘中琵鷺幼鳥未知來年同伴要否「搬屋」,新家長得怎樣,至少此時此刻圍圈發白日夢。
黑臉琵鷺全球破7000
后海灣反跌
原來記者精心挑選的5月世界候鳥日,是個誤會:5月歐洲聽得到候鳥唱歌,香港境內只有未到繁殖年紀的寥寥幼鳥,成鳥要趕向北飛,選最好的地方築巢。
天公似是嫌我們一行人的失誤未夠慘,好好的一大早竟落暴雨,記者和攝記心裏想「大鑊啦」,應該什麼都拍不到,東爺卻說鳥會同仁等了整個春天,就是在等滂沱大雨,雀鳥落地休息。方才臉仍黑的東爺幾秒間容光煥發,「你哋真係好好彩!」果不然?除了黑臉琵鷺和池鷺外,東爺表演了「聽聲辨雀」——還有一隻黃腹鷦鶯。
我們隨忘記疲勞的東爺進入米埔自然保護區,沿路邊境鐵絲網外是深圳河。北都即將讓港深創科又融合,行政會議去年已核准,範圍包括保護區外近百公頃「濕地緩衝區」的「新田科技城」等分區計劃大綱草圖;早前新田科技城司法覆核亦因申請人退出訴訟、法庭拒批更換申請人而告終。
2025年的香港,在米埔分辨港深仍容易,高樓林立那邊是深圳,涵蓋福田、南山玩樂打卡點,香港這邊是供遷徙鳥覓食的荒廢魚塘。
黑臉琵鷺屬全球瀕危物種之一。1989年,業餘觀鳥者、工程師Peter R. Kennerley在鳥會發表報告,提出黑臉琵鷺瀕危,引發保育運動潮。環團保育米埔濕地,又以黑臉琵鷺為明星物種,喚起普羅大眾關注。
身為濕地鳥種,牠需要在海邊棲息,多數分佈在東亞。運動成果不錯,鳥會統計指,其數量從2003年全球共1000多隻,升至今年過7000隻;惟后海灣(包括香港及深圳)一帶數量按年下跌逾一成,錄得328隻,亦要面對本港濕地或將減少的威脅。
目前香港境內,若要為不會說兩文三語的黑臉琵鷺找個代言人,非東爺莫屬。可是他反高潮坦白,自己對黑臉琵鷺非「一見鍾情」,1998年受世界自然基金會(WWF)邀請,研究黑臉琵鷺習性和數量時,他心中想的是「好老實……覺得只係做黑臉琵鷺好Q悶。我係想睇其他雀呀嘛!」
初中結鳥緣 「係佢選擇我」
雖然雀迷東爺曾瘋狂得為睇雀搬到米埔村住10幾年,他小時候跟許多香港人一樣,都是在城市、公屋長大的。他入坑成為生態愛好者的契機,要數英國自然學者David Attenborough的紀錄片,和小時到圖書館看各種動物書,一發不可收拾。
1986年,仍在讀初中的東爺開始睇雀。「睇咗新聞,覺得米埔好正,諗辦法點入去。」他報名WWF米埔觀鳥團,被告知需自備兩大法寶──鳥類圖鑑和望遠鏡。「鳥類圖鑑我一早搵到。」當年圖書館內1983年出版的New Colour Guide To Hong Kong Birds,東爺續借了幾十次。
他再央求父親,買一副「雜嘜牌」但也要港幣200元的望遠鏡,從家中窗戶傻傻練習對街望。整裝齊備,提早到達米埔。「結果入到嚟,我做咗傻仔!其他人冇望遠鏡又冇書,原來最認真係我。」去過米埔一次,東爺就成雀迷,1987年寫信加入鳥會做會員。當年鳥會會員多為外籍人士,寫信來往數次後,英文仍極差的東爺跟華人會員到元朗尖鼻嘴觀鳥,又與天文台前台長林超英成為雀友。
上述被他借完又借的書,近年正是由林超英翻譯和增編,鳥會出新版成《香港及華南鳥類野外手冊》。時下年輕鳥迷比東爺少時幸福:「我睇英文書係完全唔知發生咩事,淨係睇圖。嗰時圖鑑冇中文版,全部英文,我要查字典。發現就係話,原來睇多啲雀係要學英文,要讀好書。」
在藍領家庭長大的東爺憶述,「我老竇做工廠,一個星期休息一日。見佢我就知,放假攰到死,唔會做到啲咩。我怕冇時間睇雀,夾硬讀、死讀,入到大學我覺得係運數嚟」。1996年,他入讀港大環境科學系;畢業後為WWF研究黑臉琵鷺,亦以同一種鳥為碩士論文主題。
那時仍嫌研究單一雀鳥悶的年輕東爺,若不是想要累積經驗,可能不會與此鳥結緣,「某程度係佢選擇咗我」。「我以前廿四小時都喺度數雀,日頭瞓教夜晚數,全天候好天、曬、落雨都數。」他終於發現這種鳥有趣,甚至與地緣政治密不可分,團結同業及保育成果再讓他愈做愈開心;2003年,他接手「黑面琵鷺全球同步普查」的統籌任務至今,近年則有鳥會同事幫忙。
說好琵鷺故事 地緣政治也有關
黑臉琵鷺不是一開始就是明星。「2000年左右,開初其實香港人係冇乜感覺嘅。第一冇乜人見過佢,第二覺得佢個樣戇居,扁起個嘴唔知做乜鬼,又唔colourful,得白色黑色。」
東爺印象中,是2000年代周潤發與黑臉琵鷺合照的海報,甫讓這飛禽街知巷聞。那些年新聞媒體以「黑臉」和「疲勞」為標題,形容金融風暴後香港人苦,加上李克勤《花落誰家》把牠寫進歌詞,濕地公園亦用牠為標誌,於是人人認得。
「就好似《全民造星》一樣,要造出嚟,睇你點講個故事。」黑臉琵鷺故事中,觸動東爺的,是牠與邊境、禁區和戰爭的關係。黑臉琵鷺最大和成功的繁殖區是朝韓非軍事區「三八線」。「就係因為有咁政治敏感嘅地方,佢先可以唔絕種。所以我哋話睇雀睇雀,唔講政治,但原來同geopolitics係有關係。」
米埔自然保護區雖小(380公頃),模式獲東亞廣泛參考,東爺認為,其可取之處有二,一為《拉姆薩爾公約》劃其為「國際重要濕地」,減少人為干擾,二是有人員持續管理區內生態。如文首發白日夢的黑臉琵鷺,就是停在四面環水、有人定期剷蘆葦草、保持塘壆結構的濕地上。
台灣最初有人討厭黑臉琵鷺,但到了有人開槍殺牠,民情轉而珍惜鄉土,反對無止境發展,台南再成立保護區;韓國在1990年代後重視此鳥;中國內地也在2021年列其為國家一級重點保護動物(與大熊貓同級)。「佢好好彩,每個有佢嘅地方,陸續將呢件事帶出嚟。」東爺嘆做保育,不能老是悲情說「就快絕種就快絕種」,要有正面故事,才能帶來希望。
新田將發展 候鳥恐成「擠迫戶」
一隻編號為A49的黑臉琵鷺,被鳥會印了在東爺穿着的T恤上。「特登著畀你睇㗎!」A49左腳戴着白綠紅色的腳環,右腳的環是綠底白字的環誌編號。牠曾在2020年受傷,被送到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療傷。經追蹤器紀錄下,鳥會發現牠在香港及韓國間往返。東爺解釋,右腳環的顏色代表雀鳥的繫放地區,綠色是香港,藍色是台灣,紅色是韓國;左腳環的色彩組合是辨別個別雀鳥的排列。「黑面琵鷺保育網」有詳細記載。
鳥會的研究發現,有黑臉琵鷺是新田魚塘常客。不同於米埔自然保護區,其周遭的濕地為「濕地保育區」和「濕地緩衝區」,保護級別稍低,但2014年起城規會以〈規劃指引編號12C〉規定這個區域的發展項目,必須以「防患未然」的方法保育魚塘生態價值,和規定項目要符合「不會有濕地淨減少」原則。
2023年底政府公布的《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顯示,北都發展範圍包括新田濕地保育區,且已公布的保育公園面積較2021年文件中少。東爺欲言又止,說過往環團、政府與發展商曾就米埔周遭濕地「拉鋸」,維持沒有劃成保護區,也沒有大幅發展的狀態。2023年後,不少環團懷疑北都違背原則和共識。當時記者採訪北都主要推手、規劃署前署長凌嘉勤,他說環團「太敏感」,指北都能以另覓土地、修復乾塘,和促進管理的方式補償生態。
沒在睇雀的東爺又變黑臉疲勞。他不想講政策,惟擔心黑臉琵鷺下次南下過冬,新田面目全非,在這裏休息的候鳥成為「擠迫戶」。
北都計劃中,保育公園是為「補償」用。東爺覺得有點像市區重建時讓居民搬屋,可是候鳥始終不是人,人可以「不住九龍住新界,死唔去」,鳥兒不懂看地圖,「搬家」有難度。
「(發展新田一帶後)可能有幾種情况啦,可能有啲雀真係鍾意呢度,冇咗會死。都可能會轉地方又適應到。但我想講一樣嘢,我哋做保育好多時候講唔可以將責任推畀其他地區,雀仔可以飛去其他地方,所以我就唔使保育啦?黑臉琵鷺4至6月喺韓國,7到9月喺內地,10月嚟香港,3個地方都要做,先保護到佢。如果個個地方都話唔關自己事,咁就死得啦。」東爺說。
生態補償複雜 未必盡如人意
退幾步來說,如果北都保育公園盡力複製原本濕地規模和生態特性,是否能做到發展與保育並存?東爺回答我的生態學問題:「第一,你係咪真係會整先?又問你,咁點解你唔整咗先,確保有雀落嚟,先做發展?第三,所有話要整嘅嘢,有邊個係成功嘅?麻煩你講我知。」驗證生態補償的過程漫長,涉及變數眾多。以米埔為例,候鳥在此有補給,有賴魚塘中烏頭和蝦,而這又與基圍外深圳河水質好,能養活紅樹林等有關。人類再博學,補償生態仍是一條複雜——未必有解的算術。
「同埋你諗下,咁大嘅地方,有幾多人力、物力、資源放入去,但永遠係唔夠發展多。經常話千億基建,你有冇聽過一個保育計劃以十億計?每個都差(最少)一百倍。」東爺再說。萬一在香港什麼都保育不到,他考慮連結其他地區,為候鳥遷飛區做更多。
東爺任總監後已搬回市區,不過仍然幾乎日日睇雀。若能讓他選擇,他可能更想看雀而不是看發展區「大綱草圖」。1997年《大學線》採訪時問他:會否希望來世做隻雀,他說雀鳥到處遷移好辛苦,且難享受觀鳥樂趣。2025年他答案一樣:「我麻麻鍾意睇人,我想睇雀。」睇完黑臉琵鷺,他又見到麻鷹,拿起望遠鏡。人也好、雀也好,不用走,就最好。
文˙ 梁景鴻
{ 圖 } 黃志東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周淑樺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