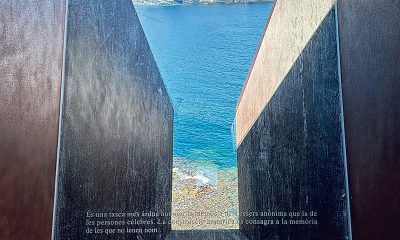副刊
無定向學堂:申官地建無家者宿舍遭拒 標籤之外 可否多一點關懷?

【明報專訊】「做了25年無家者工作,這個社會有沒有變得更包容?」上周,地政處拒絕非牟利組織「同路舍」申請,在長沙灣中產屋苑附近政府地皮設置無家者宿舍;記者除了採訪當事人、同路舍創辦人Jeff Rotmeyer,也拜訪每天為基層市民服務沒停手的社區組織協會(SoCO)幹事吳衛東(東哥)。東哥說近來已少人打電話來「媽叉」,罵無家者好吃懶做,但社會未算好包容,仍有人難接納邊緣社群。Jeff就感嘆做無家者工作最難的,是「說服港人多關懷其他港人」。
選址近西九中產屋苑 議員、居民反對
同路舍宿舍申請被拒後翌日清晨,Jeff爽快應記者邀請,到長沙灣深旺道與深盛路交界,宿舍原選址旁談感受與打算。同路舍項目總監吳兆康形容,Jeff是「衝」了過去,急切想扭轉階段性挫敗,並把握為公眾教育的契機。
雖然頂着睏意和黑眼圈,記者到達後,馬上意識到宿舍所申請選址的爭議何在——這塊地皮鄰近西九「四小龍」中產屋苑,地價不便宜。我小心翼翼道:「在這些高尚住宅附近蓋無家者宿舍,的確容易引起反對。」還是觸動了Jeff表達不忿:「那盲人、傷健人士呢?他們需要居民的批准,才可以住在這裏嗎?香港人是否相信無家者該有第二次機會,重拾人生?應該趕他們到荒島上,不應該住近民居?」
目前,未有立法會議員明顯支持同路舍宿舍申請。反對該申請的立法會議員(選舉委員會)陳凱欣批評選址靠近民居和學校,容易引起衛生、噪音及治安問題,稱數天內收到大量街坊反對。立法會議員(九龍西選區)梁文廣批評選址「極不合適」,表示學校、屋苑業主法團等持份者「清一色反對」,又指同區單身人士宿舍「曦華樓」仍有空缺。
地理學有「鄰避效應(Not In My Backyard)」的概念,形容涉及厭惡設施的發展計劃,即使對整體社會有益處,容易受到臨近地區居民反對。無家者宿舍申請風波之前,兩名議員對上一次在社交媒體就無家者議題發言,是表達無家者堆積雜物困擾社區。若代議士發言百分百反映居民意見,此類宿舍如皮球般,被居民希望踢走,不要建在本區;但議員無反對宿舍本身重要性和功能。地政總署及發展局早期回覆傳媒查詢指,非政府機構或社會企業可向地政總署申請短期租用臨時空置用地,作社區、團體或非牟利用途。有關申請獲政策局支持、相關部門確認不涉技術困難,再考慮持份者意見後,處方才會進一步處理申請。
單身人士宿舍實際宿位不夠 使用多限制
這塊400平方米的官地現時被鐵絲網攔着,石屎上是雜草和垃圾,它本來有機會變成約3層高、可供70名無家者暫住的宿舍。同路舍有在旺角、大角咀等鬧市私人單位營運無家者宿舍、社區中心和社區廚房,惟機構不靠政府資助,單憑個人和企業捐款,財政頗有壓力。於是,團隊去年開始物色租金較便宜的的官地,亦整合住宿、膳食和輔導等服務,避免目前分散在不同街區,遂向地政總署申請。
Jeff說同路舍自2018年成立以來,逐步建立全人發展的服務模式,除了提供有限的住宿資源、教育和就業轉介,職員和義工亦會嘗試了解導致無家者流離失所的家庭和心理成因,希望幫助更多人結束漂泊生活,重新融入社會。
為何堅持在市區設宿舍?Jeff解釋,「宿舍靠近市區,朋友們更容易重返主流社會」。立法會資料顯示2021年度至2022年度,全港1564名登記露宿者中,1031名分布在油尖旺和深水埗區,佔總數約三分之二。同路舍亦是因為這個原因,選址在鄰近的長沙灣。
有意見指同區單身人士宿舍仍有空缺,應先善用現有資源。不過,記者比對後發現,由社會福利署資助非政府機構提供的短期宿位為228個,由機構自負盈虧營運的宿位則為394個。疫情和過渡性房屋措施推出後,登記無家者的數量在去年12月跌至672人,仍比上述兩種宿位總數多,而且此人數或遠比無登記者少;Jeff鮮少接觸已在社署登記的露宿者,東哥也發現許多無家者沒有在社署登記。
「宿位是不夠的,但關鍵亦不在數字上,而是有否關懷無家者的需要。脫離無家的狀態是好難,該問的是當無家者住進宿舍後,有否得到進一步協助,如輔導、醫療服務,宿位私隱是否足夠,又能否安心分享自己的困難。」Jeff表示,同路舍曾協助近700人入住臨時住宿,不常設年限,曾供有需要者暫住兩年;亦聘用無家者為職員,過去兩年大約每3天,有1位所服務的露宿者離開無家狀况,且能夠自理財務;若成功覓新地建宿舍,他有心能繼續推進支援工作。
「我沒預計會被大批居民和政客反對,但最終發生,也沒讓我驚訝。我尊重他們的擔憂,只是在不了解全貌時,標籤無家者,是可悲的。連我這個不懂得講廣東話的加拿大人,都可以同理無家者,然而他們不能。」Jeff嘆。他說團隊一度認為申請將獲批,因地政總署態度友善,也完成了必要程序,沒想到遇滑鐵盧。
據Jeff了解,立法會議員們反對同路舍的申請前,沒有直接向同路舍表達擔憂;而同路舍也沒有邀請議員們討論。有否想過若有機會預先溝通,申請會更順利?Jeff認為,要求資源緊絀的小型機構去說服政客及居民,是不合理要求。「向居民叩門,請求他們的准許,我們好難做到。問長沙灣居民,他們是否覺得無家者有權利住在這區?我不敢相信這是要開口問的問題。」他說,無家者與其他人不同的,只是際遇較坎坷,強調貧窮是社會而不是個人問題,趕走無家者、視之不見,不是解決方法。未來同路舍仍會積極物色適合選址。
入住「規範化」宿舍 或逐步解決無家者問題
SoCO是社署資助的3隊露宿者綜合服務隊外,外展協助無家者的另一個機構。東哥自1999年於SoCO服務無家者,他不想直接評論長沙灣無家者宿舍申請風波,不過說政府和社會各界該反思,究竟香港需要怎樣的無家者政策,目前是「有服務,沒有政策」。
以目前為無家者提供的資助宿舍為例,無家者離開臨時住宿後「再露宿」平均達3.4次,無整全政策解決露宿問題。SoCO和聖方濟各大學日前發布的《無家者康復房屋需求研究報告》指出,六成宿位最長只可以讓無家者居住半年。「太快離開,又找不到可以負擔的單位,要去捱太空倉或牀位,可能有木蚤或者好侷,如果捱不到,有機會再露宿街頭。」不少資助宿舍設出入時間限制,如上午8點要離開,晚上11點後是門禁,不利需要夜更工作的無家者。此外,多數資助宿舍的宿位設計為雙層牀,其中需攀爬上落的的上格牀不利年齡趨老的無家者。
SoCO在上述報告中提出「先安居」和「康復住房」模式,為無家者提供穩定居所,再解決其他需求(如成癮和精神健康),提供有同儕支持、生活技能訓練、心理健康服務及醫療服務的宿舍環境。東哥說,團隊稍後會約社署和議員反映建議,在倡議政策層面仍非常間接。
2018年開始,SoCO先後由凱瑟克基金和傅德蔭基金支持,及地產商象徵式收取每個單位1元租金的方式,租用11個大角咀和長沙灣的私人樓宇單位,共有53個宿位。一來,團隊希望滿足宿位需求,二來,希望帶頭示範有效協助無家者的宿舍模式,包括有多方面支援、有私隱度、居住年期上限為兩年、不設門禁時間等。
他明白有市民和議員對無家者的觀感差,惟提醒入住宿舍本身便是解決無家者相關問題的「規範化」過程。「要禁煙、戒酒。賭錢、吸毒的當然不行了,不可能拿出來啪。無論有無這些問題,宿舍都會接受他,他自願進去,正常生活,不要拿錢去賭,去喝酒,這是一個訓練,是一個過渡期,如果找到工作,或者願意做義工,貢獻社會,其實對自己、社區和社會是三贏的。」
那宿舍是否必要在市區?不同於同路舍希望市民正視無家者為社會一部分,傾向宿舍建在市區的觀點,東哥沒特別排斥把宿舍設在較郊區。不過,東哥說無家者宿舍設立在市區,的確較能符合實際需要:「近八成無家者露宿市區,是有個原因的。露宿者大概48-49%拿綜援,另外51-52%是沒有拿,那靠什麼維生呢?露宿者要做長工是很難,多數找散工,飲食、清潔、運輸,去市區才有更多職位空缺。另外的,就真的是靠『二手飯』,你想像一下市區的連鎖餐廳是很多的,這間拿不到薯條,可以去隔籬那間。而且他們的社會資源、醫療服務,通常都在市區。」
東哥以一貫禮貌微笑解釋上述情况,記者卻聽得毛管戙。常穿印着義工活動「加油站」圖案的T恤,與無家者一起為獨居長者維修的他說,SoCO支援無家者的計劃叫「曙光行動」:「希望為無家者帶來曙光,個曙光不可以只有我們,都想個社會可以參與。」
文˙ 梁景鴻
{ 圖 } 黃志東、李紹昌、網上圖片
{ 美術 } 朱勁培
{ 編輯 } 梁曉菲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