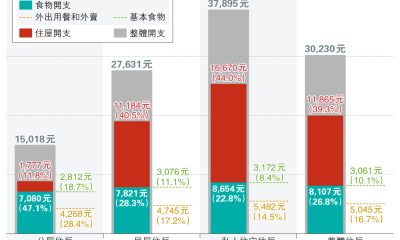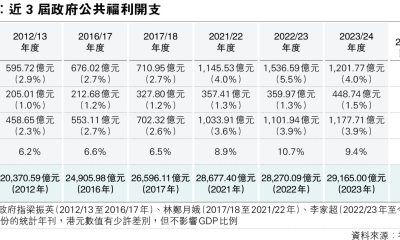觀點
王卓祺:難解互委會棄若敝屣之謎——皇后山邨食水事件有感

【明報文章】上屆特區政府最「無厘頭」之事,莫過於2023年1月1日前解散互助委員會(互委會)。翻查資料,當時亦有親中報章撰文回顧互委會曾經輝煌的一頁,如由街坊委員組織「防狼隊」保護夜歸的婦女、介入街坊之間的糾紛等等。上屆政府解散互委會所持的理由,是地區的社區服務及政府的行政架構日趨完善,互委會不復有存在的價值云云。不過,接任的一屆政府,雖然沒有重設互委會,但卻成立一個新的、叫做「關愛隊」的社區服務組織。這也客觀顯示地區確實有社區服務不足之處。可見,上屆政府解散互委會的理由,起碼對筆者來說,至今還是一個難解之謎。
讚譽關愛隊「水分」不少
香港的行政架構分為18個地區。關愛隊亦依循此一分區架構設立18個關愛隊,並於每區內再劃分若干小區設立關愛小隊。2023年第三季全港18區共有452隊關愛小隊,每隊8至12人,包括隊長及副隊長各一名。民政總署每兩年為每個關愛小隊提供80萬至120萬元資助,並鼓勵主辦團體透過贊助、捐贈或團體內部資源提供居民服務。明顯地,特區政府將關愛隊定位為地區層次的志願機構,由志願者組成。大家都知道,香港的志願機構其實並不「志願」,多數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濟及社會發展大潮中,獲得政府的財政資助。若以資助額的數目,關愛隊每年40萬至60萬元的經費,只可聘請一兩名全職或兼職人員,其他為舉辦活動的開支。若以義務志工組織來說,關愛隊要接辦政府交付的工作任務,實在不易。坊間及相關當局對關愛隊的讚譽,水分不少。
至於互委會,其性質與關愛隊完全不同;它是基層居民的互助組織,由居民選出委員組成。互委會於1976年由時任港督麥理浩正式成立,目標是改善社區衛生(當年港英政府正積極推動「清潔香港」運動)、民意蒐集和鄰里互助等。互委會最高峰是1996年,那時全港有4000多個,2010年跌至2700個,2022年3月解散前,香港還有1600個。互委會的組織,主要集中在公共屋邨。在私人大廈,政府設立業主立案法團或業主委員會。
現任民政及青年事務局長麥美娟於2008至2011年期間,曾以葵青區議會副主席的身分為互委會請命——她要求政府免除互委會繳交差餉、地租;並要求津貼金額由每季1000元增至每月1000元等。可見當年互委會得到不少社會支持。
從上述的簡單比較可以看出,關愛隊服務全港18區,不分公屋私樓,地域範圍比集中在公共屋邨的互委會大得多。然而,互委會為居民自治組織,居民參與度較高,並且有其自主性。當然,兩種地區組織並不互相排斥,均能協助政府傳遞信息、團結及服務居民。最近北區皇后山邨及山麗苑出現食水有瀝青殘留的問題,最後政府也是說會組織關愛隊向居民解說。
皇后山邨例子的細節
筆者就以住戶較多的皇后山邨說明關愛隊及互委會兩者的分別,關鍵在細節。截至2023年,全港共有258個公共屋邨,居住了200多萬人,約有82萬戶。以2021年入伙的皇后山邨作一個案深入分析:7座大廈居住了8865戶,約2.36萬居民。試想一下,這個居住了近9000戶的屋邨,憑藉一個關愛小隊8至12名志願隊員,如何提供服務?若用上現代通訊方法如WhatsApp或電郵,對於上了年紀的長者或文化程度不高的居民,效果有斟酌空間。故此,食水事件中,特區政府也聲稱要調動總共6個關愛小隊,即由鄰近小區抽調5個過來,再加上區議會及「三會」(民政總署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成員,超過50人,向居民解說食水安全的問題。
若皇后山邨有互委會的話,7座大廈各有一個居民自助組織之外,每層樓還可以有一個樓長。他們可以直接拍門聯絡街坊,或打電話溝通;甚至臨時「拉夫」組織更多熱心街坊,便能迅速通過組織框架及街坊網絡將通報傳遞予居民。這個基層網絡與從外而內的關愛隊在鄰舍層面的對比,便清楚不過了。關愛隊隊員多是邨外義工,與邨民關係還是隔了一層,缺乏同邨的情誼。若關愛隊能像專業的社區工作者,組織居民自助,成立類似互委會的居民組織,這便可與居民站在同一陣線。不過,關愛隊的性質改變了;它不是傳遞關愛,而是社區組織,兩者所要求的工作方法及技巧有所不同。
互委會的政治作用
2023年區議會選舉(地方選區界別)只有119萬人投票,投票率為27.59%,見歷史新低。2019年那一屆區議會選舉,發生在黑暴肆虐半年之後,但投票率特別高,達到71.23%。兩屆對比十分「礙眼」,亦令有關當局宣稱香港「由亂及興」尷尬不已!今年12月7日又是另一次立法會選舉,相信投票率亦不會高。
2019年動亂之前,確實有政黨為了爭取選票,積極拉攏互委會支持。但在全國人大頒布「完善選舉制度」決定之後,並引入資格審查,反中亂港者參選機會不大。但問題的另外一面是政治立場「清一色」,選擇少了,以前支持「泛民主派」的選民便索性不投票了。
在這樣的政治形勢下,再加上立法與行政關係良好,90名立法會議員缺少了表現的機會,又如何引起選民的投票意欲呢?况且不少議員不見經傳,相信大多數選民連90名議員的姓名也記不齊。連認識也缺乏,怎會有投票的興趣呢!相信12月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再見新低也不出奇。特區政府的治理效績,也可起催票的作用。但是當前經濟環境半死不生;「住得貴」、「住得細」、「住得舊」的居住問題進展不大;就算在「由治及興」的階段,這屆政府亦棄用國際通用的貧窮線量度扶貧成績,但至今近3年卻還未有替代方案,使人懷疑今屆政府是否有心解決這個一直困擾特區的深層次矛盾!特區政府又缺乏一些振奮人心的大計,除了托國家鴻福,DeepSeek橫空出世,外資亦來攙和香港這一池股市溫水!整體而言,在政治及經濟悶局相當之下,實有神仙難變之嘆!
內地政治制度、城市基層治理,在區級政權之下有街道辦事處之設,是市政府的外派機構。而街道辦事處之下便是居民自治組織的居民委員會,與香港的互委會十分相似。居委會也可以說是政府的「神經末梢」,在城市這個「陌生人社會」打造熟人的關係。香港鄰舍層面的互委會也有類似功能,將城巿中的「陌生人」連結起來,增強社區的歸屬感。舉例說,在以前東華三院《歡樂滿東華》籌款的屋邨比賽,亦有賴互委會的助力。
重建互委會 激活地方行政「神經末梢」
對於高度城市化的社會如香港,居民住在高樓大廈之中,鄰舍之間的接觸甚為困難,發展居民組織並不容易,因為城市人的居所通常並非其經濟收入的所在地。鄰舍守望相助的精神,不易發揮出來。不過,相對於私人大廈,公共屋邨又較容易發展鄰里關係,除了每層戶數眾多之外,公共屋邨居民流動性較低,而且屋邨的商場、街市、食肆都是街坊容易碰頭之處。這些有利因素,才能化解大城巿組織「陌生人」的痛點。
人是感情的動物,香港目前政治情勢不利講政治;催谷選票還望拉攏關係搭夠。况且,香港社會基層居民最重實際,不尚空談;支持政府利之所在。2019年黑暴之亂並不發生在公共屋邨之內,便是明證。展望將來,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對支持者選區投桃報李的做法,亦有值得借鑑之處。組織互委會及業主立案法團,一直是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的專長。相信這批擅長聯絡及組織互委會的聯絡主任還在職,由他們推動重建互委會應事半功倍,這樣便不難再次激活香港地方行政的「神經末梢」。相對於關愛隊,協助組織鄰舍居民互助組織,對於政府來說,所費無幾——只是公共屋邨地下讓出一個空置單位,再加上每季津貼二三千元;最關鍵還是民政事務處聯絡主任拍拍膊頭,重啟街坊的合作關係。往日互委會功能式微之說,不外是「官字兩個口」!行文至此,恕筆者智窮,還是想不出當年特區政府為何如此「無厘頭」將互委會棄若敝屣呢!
作者是新範式基金會資深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高級名譽研究員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王卓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