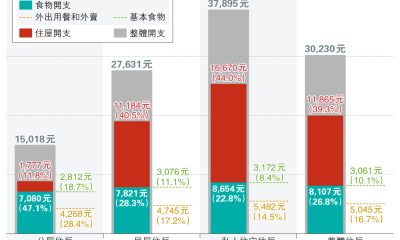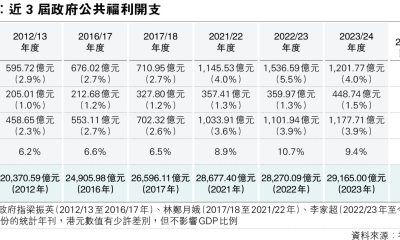觀點
王卓祺:文化承傳及歷史記憶──內地旅遊找到的民族認同與國家安全聯想

【明報文章】前言
本文由以前撰寫過的國家認同研究所獲得的一些心得,再加上近幾年在內地旅遊的點滴觀察,再結合當前國家安全的話題綜合而成。國家安全的道理並不複雜;筆者理解,有國家認同才有國家安全;而國家安全之本,在於文化認同及歷史構成的命運共同體。而文化者,實乃生活實踐所構成的,脫離不開生活體會所產生的觀念、規範和價值(下文會為文化下一定義)。而歷史是過去發生的事情的記錄;不過,記錄什麼有選擇性。大家或許記得清龔自珍講過:「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
英治期間當然不喜歡治下的中國人認同中國,最好是當「黃皮白心」親英派,次而作殖民地順民。回歸後一國兩制,中央政府亦容許香港人不認同共產政權;總結2019年修例風波,才搞出「愛國者治港」,其前提是認同中國共產政權。這個曲折發展,有其歷史演變的邏輯,亦即以前的寬大種下了以後的嚴厲。今天看來,黑暴分子數典忘祖是有迹可尋。當年中央政府若不是懷着一番好意,只是「空着急」地不斷要求特區政府履行憲政責任,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而已。若中央政府早點「自己來」,便沒有日後的黑暴肆虐。但這觀點缺乏歷史限制的認識。若從文化及歷史角度看,《港區國安法》只解決了國家安全的硬件,但卻解決不了「軟對抗」背後對中國國族的認同問題。
黑暴分子與內地青年人傳統民族服裝熱潮對比
2019年修例風波走出了一小撮黑暴分子,不單止反共,更加反華。這批人未經歷過共產黨的統治,卻好像與共產黨有血海深仇。但在共產政權生活的年輕一代,卻更認同中華民族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具體例證是颳起國服潮——漢服及少數族傳統服飾。這個穿著傳統民族服飾的潮流,是筆者近年在內地旅遊感受最深的一個現象。
一批批的年輕人,尤其是少女,穿著漂亮的傳統民族服裝及飾物。例如在雲南省西北端的香格里拉,相信是漢族青年人,穿著藏服在大街小巷及旅遊景點打卡;西南端的西雙版納,穿的卻是傣族、納西族等少數民族服飾。當然在漢族人聚居地,筆者近年遊覽過的南京、揚州、興化、福州,以至西安、成都,見到多的是穿傳統漢服的少男少女。這個源於2000年初興起穿著傳統民族服飾熱潮,背後的推動力是民族及文化認同,尤其是年輕一代對國家崛起有更大的期盼及自豪。
文化承傳的問題
翻查資料,漢服潮也引起一些爭議,尤其是有人認為「漢服運動帶有民族主義色彩,甚至帶有排他性,過於強調漢族的傳統,排斥其他民族」。其實,任何一個運動或潮流,一定有一小部分人走偏鋒;觀乎內地少數民族地區漢族青年男女穿著少數傳統民族服飾,便看到中華民族的包容性。如果這個漢服潮有排他性的話,也與香港的一小撮黑暴分子,在國家權力缺位下,聲稱香港是一個「香港民族」,要「時代革命」、「光復香港」云云;他們一定比到目前為止,所見所聞的所謂「大漢族主義」,何止偏激100倍。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文化的定義:「某一社會或社會群體所具有的一整套獨特的精神、物質、智力和情感特徵,除了藝術和文學以外,它還包括生活方式、聚居方式、價值體系、傳統和信仰。」若從此定義來看,穿著民族傳統服飾的潮流,只是文化的一個小部分而已。推論至香港修例風波的黑暴分子,其煉成便應有更多的文化內涵。他們一定浸淫於一套異於內地那套中國文化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傳統及習俗!不然,他們怎會於遊行期間高舉美國旗,又高喊「美軍來了我帶路」的口號。這種中國人認為的漢奸行為,不會是一日煉成的。
港區國安法實施至今,香港特區改變了什麼生活方式、價值觀、傳統及習俗呢?以筆者理解,改變不大,除了少了「政治雜聲、噪音」之外,還有不少非暴力、隱蔽性、蠱惑人心的「軟對抗」。根據上文的文化定義,其他文化內容的生活實踐還沒有什麼重大變化!若這觀察是對的,國安法治下的特區,人心還未真正回歸,「軟對抗」亦不易靜止。在這個背景下,探討國家安全文化之本有深一層的意義。
歷史記憶的問題
黑暴分子數典忘祖,事出有因。數典忘祖成語出自《左傳.昭公十五年》,講述晉國大夫籍談在周景王面前,列舉一堆典故,卻忘記了自己家族是負責掌管晉國典籍的官員,周景王因此批評他們數典而忘其祖。這個典故也適用於反對派及黑暴分子,他們最重大錯誤是忘記了香港是中國近代史「百年恥辱」的開端。這個近代香港歷史的「祖」——鴉片戰爭割讓香港的恥辱,使香港街頭的「港獨」暴動不可能得逞。
回歸後,基於種種原因,中央政府並沒有在香港推動去殖民地化。在這個背景下,一小撮黑暴分子認賊作父,便變得不出奇了。加上一個「八九天安門事件」,反對派年年「六四」遊行,好像中國歷史在那一刻凝結了。我們稱之為「斷裂」的歷史觀。這個「斷裂」的歷史觀只解釋了反對派反共的一面,卻未有解釋黑暴分子反華數典忘祖的根源!
最近與友人去了一趟陝西銅川「藥王」孫思邈的故里參觀,有一點體會與大家分享。這位唐朝一代名醫的家鄉,在每年農曆二月初二便舉辦藥王廟會。藥王故里在今天銅川市的耀州區,只是一個普通的市轄區,但在歷史上卻出了一位名醫。銅川市還興建了一座建築面積1.53萬平方米的孫思邈紀念館,成為銅川旅客必到的景點。可以說,孫思邈成為銅川人的歷史記憶——今天的銅川人一定記得1400多年前銅川(唐京兆華原)出了一位名醫,被稱為藥王。若你是銅川人,你會否數典忘祖呢?
銅川出歷史名人並非孤例。近年我去過的福州,便出了位近代民族英雄林則徐,還有著名翻譯家嚴復及詩人冰心等。在小小的江蘇興化,也有宋代文武兼備的范仲淹、清朝書畫家及文學家鄭板橋,以至《水滸傳》的施耐庵。今天居於這些前人故里土地上的人,不一定與前人有血源關係,但隔代同鄉之誼亦與有榮焉。那些以前同一土地上發生的種種歷史人物及故事的記憶,已融入每個鄉土人士的血液中!中國人的身分認同怎會是問題。
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巿,回歸後人口也穩定下來。回歸一代,正是戰後移民的第三代,正是這一代出了不少黑暴分子。筆者年幼才赴港定居,還記得兒時在家鄉生活的一鱗半爪,並間中回鄉省親,記得在家鄉祠堂祖父輩的輩分。但是,大家想像一下,香港這樣城市化的社會,除了新界的原居民外,青年一代若斷了與鄉土的血源紐帶,是不容易有家國情懷呢!這一代也是網絡世代,相信亦少有翻過或翻齊中國的四大名著,薰陶一下傳統智慧及價值。香港傳統的節日只當為假期,背後的歷史文化涵意亦少提及。這些例子還有不少!
總結
無可否認,近幾年特區政府推動的國民教育成績不少,尤其是內地考察團開拓了青年人對祖國的認識及認同。國家進步及成就亦有目共睹的。不過,民族及國家認同是主觀性,有情感溫度的。中華民族的文化承傳及共同的歷史記憶,才是最難培養的,尤其是對於已有成見者。在這個脫離中國文化及歷史源流的中國人社會,中國人的根需要刻意栽培!小小的銅川,也為了紀念孫思邈而興建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紀念館,以壯銅川人的歷史自豪及記憶。香港是近代中國「百年國恥」的起點,卻對鴉片戰爭及民族英雄林則徐沒有刻意記憶。這真的有點不好理解。對付黑暴分子及其同路人,嚴格按照港區國安法執法,仍然是最有效。但是,國家安全要軟硬兼施;此文在「軟攻」方面作一兩點補充而已。
作者是新範式基金會資深研究員、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高級名譽研究員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王卓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