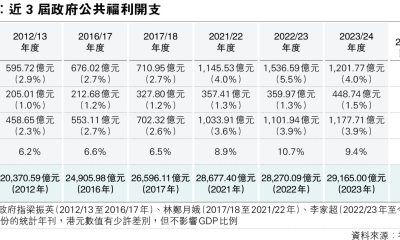觀點
張炳良:鑑往看今:公務員改革的空間與焦點

【明報文章】「完善」選舉制度及厲行「愛國者治港」下,中央為特區的治理體制打通內外經脈、去除障礙,議會拖拉及社會泛政治化已成過去。新制考驗特區治理能力和效能。現屆政府開局宣示「以結果為目標」,近期吹風「高級官員責任制」,皆欲強化政府內在的績效管理。財赤壓力下,要求改革公務員制度的呼聲漸多。改革有必要,也存空間,但需目標清晰、聚焦務實,鑑往看今策未來。
成也官僚 敗也官僚
成也官僚,敗也官僚。改革官僚最終仍需透過官僚去落實,要爭取其認同,避免對立分化。把改革基因植入體制深處,涉及行為文化和生態上的長遠改造。
韋伯(Max Weber)的官僚體制「理想型」,集理性專業、法理權威和分工科層架構於一體,有助效率與質素。可是實踐下來,官僚主義卻成為政府失效寫照。官僚之惡包括尸位素餐、文山會海、浪費資源、貪腐濫權等。行政經濟學早就批判官僚「預算最大化」(budget maximizing)、「機構最大化」(bureau maximizing),及層級架疊、因循避責避險的行為。
1980年代美國總統列根曾有名言「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government is the problem(政府並非我們所處問題的解決辦法,政府本身就是問題)」,那時歐美颳起批官僚、崇市場之風。但在亞洲,「四小龍」經濟奇蹟卻成為官僚病與體制效能並存的悖論佐證。
九七回歸時,香港經濟欣欣向榮、治理似井井有條,中央和本地社會高度肯定繼承自港英的公務員制度的優越性和韌力,尤其作為骨幹精英的政務官系統。但時移世易,隨着外生危機及內在社會政治矛盾衝擊,特區政府表現愈受批判,公務員漸成各方攻擊的主要對象,什麼懶政避事、缺乏擔當等。
2019年暴亂,執政團隊和議會駕馭不了大局,進退失據,惟受責較深的是政務官,公務員政治忠誠受質疑。2024年修訂《公務員守則》,強調維護國家憲制秩序及國家安全、效忠政府、績效問責。
行政改革往軌
20世紀西方追求公共行政效率、強調科學管理,1960年代已仿效私企「目標管理」(management by objective),1970年代鼓吹「企業管理」模式(corporate management)及「企劃預算」制(planning programming budgeting system),並因財政危機惡化而發酵私有化、市場化改革思潮。
1990年代,新公共管理主義(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及「再造政府」運動登場,推動企業化,重視績效管理、扁平結構和權責下放,改造官僚體制之基因。當選舉政治和官僚系統雙重失效時,改革者求助於市場機制,倡議私營及公私合營、績效預算、薪效掛鈎等。但之後出現異化,利潤邏輯凌駕服務倫理。
香港過去改革也多。英治時期於1970年代中後期實行《麥健時報告書》管理改革,便帶有當時新企管的影子。1978年接納新成立廉政公署之防止貪污處建議,頒令各部門實行「上級問責制」(supervisory accountability),若有下屬貪污枉法、疏忽職守,上級難辭其咎。原則上各級公務員都要問責;當然,他們跟2002年起政治委任的司局長要負的責任,屬不同性質和層次。但當薪酬獎懲制度僵化、職業超保障、與表現脫節時,則問責名存實萎。
港英晚期突顯效率政治,推行公營部門改革:下放資源管理權力、靈活調配、引入市場機制(外判外購)、績效導向、服務承諾、基準預算(baseline budgeting)等。回歸初期,亞洲金融風暴導致經濟衰退、財政緊絀,厲行「資源增值」,支出封頂,惟容許部門自行支配效率節約所得(efficiency savings),並要求重排優次、重組結構與流程、善用公私合作。
回歸初改革不逢時
董建華首屆政府早於1999年便推出公務員體制改革,冀建立21世紀較開放型的公務員架構:進出靈活、基本職級(佔編制三分之二)實行合約制、中層可向外招聘(非只內部晉升),並引入績效為本的薪酬制度以吸引、激勵及挽留人才,貫徹服務型管理文化。若能成事,香港會成為改革創新典範。
領軍改革的時任公務員事務局長林煥光,曾借用英國已故首相戴卓爾夫人「TINA」名言(there is no alternative;別無他途),說不自我改革便被人改革。歷史的諷刺是,公務員改革最終慘敗收場,主因是改不逢時,經濟不景造成人心惶惶,改革「顛覆性」過大,公務員不分上下疑心重重,士氣動搖,工會反對。2000年轉向凍結公務員招聘(不過容許短期非公務員合約人員),並推出自願離職計劃,壓縮編制。到2006年經濟復蘇,才恢復公開招聘。
2002年政府成立專責小組檢討公務員薪酬政策及薪酬制度(我為成員之一),第一階段報告書大膽建議有限的薪效掛鈎,中期先在首長級試行彈性的「薪酬幅度」制(pay ranges),長期把薪酬管理權力下放至部門管理層。但遭強烈反對,各部門管理層均有保留,最後不了了之,也再沒有第二階段研究。
2002至2003年一場公務員立法減薪風波,造成官職雙方前所未見的對立,工會抗議遊行。雖然最終挑戰減薪合憲性的司法覆核失敗,惟政府的政治元氣大傷。自曾蔭權政府以來,再未重啟公務員制度改革或公營部門改革。2008至2009年全球金融海嘯後,新自由主義衰落、NPM式微,國際上行政改革也失去方向。
重思改革 聚焦人才績效
重啟公營部門特別是公務員改革,應汲取過去及他地經驗,並避免戰線過長、張力過大。改革目標可放在:聚人才、求績效、靈活開放、擇優提拔、權責相稱,進程由淺入深。
(1)聚人才,求績效。公務員薪酬水平維持與大中企業對比,原則上能維持吸引與挽留優秀人才的競爭力。傳統公務員體制過於封閉和同質化,只在基本入職級別公開招聘,晉升以內部及年資為主。需活化「進」及「出」,考慮在一些能轉移企業或非政府機構經驗的職系,加入中高層外聘,部分首長級職位跨部門及對外開放競爭上崗,有助引進新視野,豐富系統整體的勝任能力(competencies)。
對表現不濟的人員敢於懲處終聘,但盡量激勵改善,及對表現優秀者提供轉調相近其他職系再發展的路徑,讓政府培養多元能力人才,並注重擴闊視野和工作滿足感(job enrichment),資源容許下借調中層往非政府機構,加深了解業界操作和社會實况,使更能「接地氣」。人才難求,制度上應針對留不住人才的反誘因(註1)。
目前公務員薪酬制度承襲以前英制,並與複雜的職等結構緊扣。由於政府不少工種缺乏私企業界類比,多靠內部職級掛鈎,觸一髮而動全身,調整易生爭議,造成固化及與時代脫節。也有質疑公務員生產力和增值如何衡量、能否與私企相比。
公務員「物有所值」,不是指循規蹈矩、勞勞役役而已,而是能否切實解民解業所困、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公平的績效評核能激勵士氣表現,馬虎則製造怨氣與抵制。過去幾年較多講規範紀律,以端正隊伍,「保底」後應多激勵誘因。
績效定薪,知易行難,因為政府工作表現涵蓋面闊,既包括工作達標,也涉及法律、程序、操守、服務質素、公平公正等,變數多,難定量。在西方薪效掛鈎曾經成一時風尚,但姿勢多於實際,未成氣候(註2)。薪酬制度既要保持基本穩定,當今國際及企業趨勢日重績效和新技能增薪(progression)。如何結合三者、透明公平,乃改革的再平衡所在,較有針對地去激勵表現。
(2)擇優提拔,權責相稱。年資愈長、經驗愈豐富,也反映對機構之忠誠。惟提拔不能太靠年資,或以晉升作為獎勵在原崗位表現的手段,以免墮入「彼得定律」桎梏。有主張局部開放競爭晉升高位,但須機制公平,當任者才有正當性。同時,應為中高層公務員「充權」,強化首長級(尤其D2層)的權責,使有發揮空間,並重視部門首長地位,不動輒由司局長出頭。儘管整合政府(joining up government)達至一體化十分重要,排除跨部門拖拉,但也需鼓勵擔當,避免事事靠最高層統籌拍板,致過於中心化、層級臃腫、權責上推。
去除虛妄 務實而行
改革切忌虛妄,接受現實中不存在完美「善治」,一切乃相對而言。行政主導也不等於一切行政化,單靠改革公務員表現,不能解決治理上所有問題。
所有改革節點,均保守與創新因素並存。由此產生的改革之旅,始終是一個再平衡的妥協過程,挑戰在於營造對改革的持份與誘因,化懷疑為認同(註3)。漸進但累積的改革,較利妥協和共識,細水長流,水能穿石。
註1:近年首長級政務官流失較多,有說他們寧轉職因不喜歡「政治工作」。是耶非耶,為何「去泛政治化」後仍有過多壓力?
註2:薪效掛鈎主要面對兩大挑戰,(1)公營部門工作和結構十分複雜,並受經濟、政治和法律環境影響,不少服務涉跨部門及團隊合作,評核不能簡單,並要求公平透明;(2)薪效掛鈎對激勵員工及服務質素的實際作用不明顯,視乎不同工作範疇和組織生態,須因地制宜(fit for purpose)。參考OECD (2024) Salary systems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their reforms. SIGMA Paper No.71. Paris: OECD.
註3:國際行政改革比較分析,可見Anthony B. L. Cheung (2020). Administrative Reform: Opportunities, Drivers, and Barriers. In B. Guy Peters and Ian Thynne (eds) Oxford Encyclopedia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是前運輸及房屋局長(2012-2017)、香港教育大學前校長(2008-2012,時稱香港教育學院),現為教大公共行政學講座教授及顧問
■稿例
1.論壇版為公開園地,歡迎投稿。論壇版文章以2300字為限。讀者來函請電郵至[email protected],傳真﹕2898 3783。
2.本報編輯基於篇幅所限,保留文章刪節權,惟以力求保持文章主要論點及立場為原則﹔如不欲文章被刪節,請註明。
3.來稿請附上作者真實姓名及聯絡方法(可用筆名發表),請勿一稿兩投﹔若不適用,恕不另行通知,除附回郵資者外,本報將不予退稿。
4. 投稿者注意:當文章被刊登後,本報即擁有該文章的本地獨家中文出版權,本報權利並包括轉載被刊登的投稿文章於本地及海外媒體(包括電子媒體,如互聯網站等)。此外,本報有權將該文章的複印許可使用權授予有關的複印授權公司及組織。本報上述權利絕不影響投稿者的版權及其權利利益。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張炳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