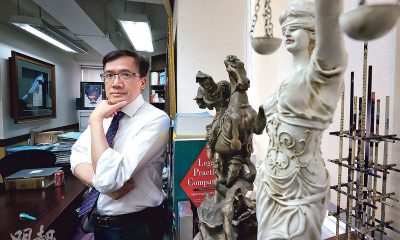副刊
夏雙周:如何記憶二戰:英雄還是受難者?

【明報專訊】2025年是二戰結束80周年,各國都有盛大的紀念活動。在英國和法國,除了鋼琴音樂會,亦有小規模的軍事演習,還有政治領袖針對俄羅斯的強硬表態。在德國,既有政要表達應繼續汲取戰爭教訓,維護和平的聲音,亦有右翼政黨反對所謂「恥辱崇拜」(cult of shame),要幫助年輕人卸下戰爭原罪包袱的不同政見。俄羅斯則仍是紅場閱兵,紀念衛國戰爭勝利80周年,既表達對於西方人忽視俄國人為二戰作出的巨大貢獻和犧牲的不滿,亦表明誓死捍衛俄羅斯生存權的決心。在中國,舉世矚目的9‧3閱兵亦已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後英雄記憶文化的來臨
歷史敘事的建構,總是基於記憶和遺忘。二戰後,歐洲出現了一種新的記憶戰爭的方式,即所謂「後英雄記憶文化」(post-heroic memory culture)。19世紀的歐洲,記憶戰爭的視角,主要是一種與國族主義有關的英雄浪漫主義。國族主義起源於法國大革命,此後透過拿破崙戰爭(1803-1815),擴散至各個軍事佔領區,並在歐洲蔚為風潮。受此風潮影響,紀念戰爭中陣亡戰士的方式,亦發生了顯著變化。過去,陣亡者的遺體通常被遺棄在戰場上,任其雨打風吹,無人過問。國族主義興起之後,殞命沙場的戰士被當成民族英雄,由官方永久埋葬,甚至設立紀念碑,以及有統一墓碑的紀念公墓。新習俗還包括於公共場所豎立英雄雕像,供國人膜拜,風氣所致,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和20世紀初期的法國都一度出現了「雕像熱」(statue mania)。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爆發後,這種將戰死官兵浪漫化的英雄主義在歐洲開始受到質疑。由於重炮、機關槍的應用,以及將氯氣和光氣這些毒氣作為攻擊的武器成為新的戰爭手段,殺戮變得更加容易。一戰中死亡的士兵高達千萬,平民的死亡人數甚至更高。如此暴力血腥的戰爭手段,如此高的軍民死亡人數,儘管官方仍試圖將馬革裹屍說成是高貴的、英雄的行為,已經很難再令人產生共鳴。因此,一戰是歐洲人記憶戰爭方式的一個轉捩點,從將戰爭中被殺的軍人描述成主動為國犧牲(sacrificium)的英雄,逐漸過渡到將其定位為被動的戰爭受難者(victima)。
將人作為工具,甚至戰爭炮灰的做法,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變本加厲。大屠殺、萬人坑、集中營、大饑荒、強暴婦女、驅逐出境,還有近2000萬歐洲人的死亡,使得二戰成為歐洲歷史上的至黑時刻。當然,二戰甫一結束,對於戰爭的論述完全由戰勝國主導,戰敗國沒有任何發聲的機會。戰勝國將自己描述為世界的解放者,為此而死的戰士是為反法西斯事業光榮犧牲的英雄,永垂不朽。在不分前線與後方、全民總動員的總體戰下,敵國人的死亡,無論是軍人還是平民,則不過是戰勝國的勝利成果,死不足惜,甚至死有餘辜。
然而,一種後英雄記憶文化正在興起,尤其在德國與日本。作為二戰最初的發起國、最終的戰敗國,它們無法將本國視為勝利者,亦無足夠正當性將死去的國人當成英雄,於是這些國家開始將其看成受難者。它們將國人一分為二,一小撮的「真正的加害者」和大多數無辜平民。加害者已為戰爭付出代價,而無辜平民亦是戰爭的受難者,現在因為戰敗正在承受痛苦。借助該論述策略,德、日逐漸淡化曾是戰爭中「加害者」的身分,並成功地掩蓋了即使是平民,無論是否有意識,亦曾擔任過法西斯的「幫兇」的事實。尤其在日本,因為曾二度遭遇美國的原子彈襲擊,很多日本人對於二戰的記憶幾乎等同於原爆「受難者」。之後,大量的受難者團體出現,積極分享他們在戰爭中的痛苦經驗,獲得媒體的關注,成為了受難歷史的證人。大量與受難者有關的紀念館、展覽廳紛紛建立,其中的圖片、實物和遺蹟,亦成為歷史的證據。這些證人和證據,使得這些受難者身分獲得正當性。當經歷過二戰的人逐漸凋零,這些紀念館成為後人關於二戰的記憶之場,後英雄記憶文化不僅得以形成,並以人權、和平的名義,在全球產生影響力。而「受難者認同」亦成為將歐洲人聯合起來的黏合劑。
▓英雄敘事和受難者敘事之間
中國人對於抗戰的記憶亦經歷過幾次轉折。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無論對於剛剛結束的國共內戰,還是之前的抗日戰爭,都是將其英雄化、浪漫化。中共的建政,既非透過選舉,亦非依靠政變,而是長期的軍事鬥爭。毛澤東自認,中國的革命經驗為世界共產運動找到了一條可行的成功之路,那就是「武裝奪取政權,戰爭解決問題」,和平手段無法推翻資產階級,只有軍事手段才行。故此,毛時代形成了一種崇拜軍人、浪漫化戰爭的政治風氣,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建立即為明證。領導正面戰場對日抗戰的蔣介石,被描述為「不抵抗」的賣國賊,而抗戰勝利的功勞,屬於中國人民,尤其是堅持抵抗的八路軍、新四軍。毛澤東和蔣介石一樣,都主動放棄了要求日方實行經濟賠款的要求,但目的不同。蔣介石擔心一旦要求賠款,無疑會把日本政府推向共產黨一邊,遂決定不妨「以德報怨」。毛澤東做的則是階級分析,要求戰敗國賠償是帝國主義行徑,為社會主義國家所不齒。日本人民長期為少數軍國主義分子壓迫,一旦要求賠償,資產階級會將經濟壓力轉嫁到日本人民頭上,人民的生活就會雪上加霜。毛時代的視角,頗類似後來德、日將戰爭中的國人實行二分的論述策略。在此政治氛圍下,龐大的受難者群體因其不符合英雄敘事之需,不僅被忽視,甚至被故意遮蔽。
進入改革開放之後,隨着階級鬥爭的論述逐漸被拋棄,現代化敘事取代革命敘事,抗戰的記憶文化亦隨之發生變化。鄧小平急於發展經濟,並將眼光投向鄰國日本。他公開承認,「我們是個落後的國家,需要向日本學習」,甚至親自訪問日本,尋找當年徐福想找的「長生不老藥」,即實現現代化的秘密。日本的政治精英為了民族尊嚴,不願為發動侵華戰爭向中國公開道歉,但願意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對日本來說,向中國提供資金和技術,雖無賠償之名,卻有賠償之實。於是,日本的對華援助,成為中國現代化初期最重要的外部動力。在中日合作的氛圍下,與戰爭有關的議題被淡化,甚至迴避。
在中國實現現代化後,國家變得自信,受難者敘事亦開始出現。1995年,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大會上,時為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指出,抗日戰爭中,中國人的死亡人數高達3500萬,經濟損失則達至6000億美元之巨,故此,中國開始承認自己是世界上於二戰中損失最大的國家。而中國民間亦在積極推動受難者記憶文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京大屠殺。發生於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殺,曾一度是南京國民政府不願提及的事實。發生於首都的屠城事件,不僅是民眾的災難,亦是國家的羞恥。交戰中的國民政府,不願因此消磨士兵及民眾的抗日士氣,一直採取淡化的宣傳策略。但到了1980年代,受到全球尤其是日本的受難者記憶文化的影響,中國的受難者群體要求政府承認自己在戰爭中的付出,甚至要求日本政府給予賠償。此外,民間歷史積極分子、南京當地民眾亦都希望政府有所作為。1982年,日本右翼人士開始修改歷史教科書,將「侵略」改為「進入」,令中國政府極度不滿。故此,1985年,中國政府建立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從此中國亦進入了一個記憶抗戰的新時期,轉向強調集體苦難。然而,受難者記憶固然可以令中國博取同情,佔領道德至高點,惟令中國政府顯得無能,而非強大,並非北京所願。於是,與德、日由受難者敘事主導不同,中國的記憶文化是一種勝利者與受難者兩種敘事的混雜,政府既要突出中國人是受難者,但又不想示人以中國政府軟弱無能、無法保護國人之感,但兩者都要,有時無法做到,畢竟兩者是矛盾的。
近10年來的記憶文化則有重回英雄主義敘事的趨勢。2014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集體參加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可謂史無前例。中國官方亦開始將9月3日,即日本向美國投降、簽署正式文件的翌日,定為「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日」,並於2015年首次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紀念大會和閱兵式。時隔10年,此次再次「9‧3閱兵」,可見北京對於「抗日精神」的重視。
文˙毛升
編輯˙林曉慧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