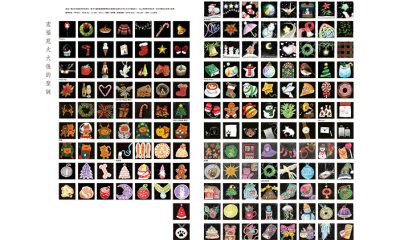副刊
ways of seeing:俯瞰日佔香港:戰時航空照片作為史料的應用與價值

【明報專訊】第二次世界大戰對香港造成廣泛破壞。這個城市經歷了一次激烈的戰鬥(1941年12月8日至25日的香港戰役)、日本佔領與軍政(1941年12月25日至1945年8月30日),以及盟軍多次轟炸(1942年10月25日至1945年6月12日)。至戰爭結束時,城市已滿目瘡痍,市面亦接近饑荒邊緣。戰前,香港人口達150萬,至戰爭結束時只剩下約50萬至60萬,死難者難以計算。這個時期更對香港的歷史紀錄帶來浩劫,無數檔案與私人紀錄因為戰爭與其後的顛沛流離而永遠消失,即使官方檔案亦殘缺不全,為後世研究帶來不少困難。
民間、官方日佔史料續面世
有關香港在這個災難時期的歷史,多年來卻有一種神秘色彩。這不但是由於戰時資料佚失,亦因為不少時人因種種原因而避談這個時期的經歷。部分以往非常流行的敘述採用了幾乎獵奇的角度與手法描述這個時期,更加插了不少誇張的內容,資料亦時有含糊不確之處。這些內容不時被後續的研究者徵引,形成不少真假難辨的「都市傳說」。另一方面,有關日據時期的研究亦日漸增加,範圍包括社會民生、地下抵抗、戰俘與拘留者生活、佔領政策、合作者問題等,可見這個時期仍得到不少關注。
近年,仍有各種日佔相關史料從不同渠道被發現。這些新史料使我們對日佔時期的管治、軍事、社會、抵抗和情報工作,以及戰後復原與戰犯處理均有更深入的認識。它們部分來自本地,例如近年出版的律政司晏禮伯(Chaloner Grenville Alabaster)和天文台副台長希活(Graham Heywood)的日記,以及零星日軍人員的紀錄如相簿等。其中市民潘廣樑的筆記更顯示民間之中尚有極具價值的歷史資料(見《潘廣樑札記:一個香港人的時代紀錄1920-1970年代》)。此外,香港歷史檔案館的各種檔案,如日佔時期總督部清查香港物業的紀錄(「家屋登記」及「敵產台帳」)及不同企業(如東華三院、香港社會發展回顧、太古、匯豐)的檔案亦得到更多的運用。一些為人熟悉的史料亦因為新方法得以有更大的價值。例如,日據時期電話局出版的《日本人關係電話番號》(即電話簿)所載的資料被加進「日據香港互動地圖,1941-1945」(見bit.ly/4g81O5D),使我們對當時社會經濟狀况及其空間背景有更深入的理解。《電話番號》中對日本海軍設施的內容,使我們得知日軍慰安所等設施的實際位置與空間佈局和背景。與戰爭相關的遺址近年亦有不少研究,特別是散落香港各地的戰時軍事建築。這些研究突出了港九新界各地在戰爭不同階段的各種經歷。
美軍航空照 重現已消失建築
近年新發現關於日據香港的史料中,較重要者可算是戰時航空照片。2023年,香港浸會大學香港空間史研究計劃(Hong Kong Spatial History Project)團隊在美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的目錄中,發現了美軍拍攝的香港航空照片。現時,團隊蒐集了大約300張照片,這些照片涵蓋了香港島、九龍、新界、離島,以及深圳寶安等地。這些照片大多屬於垂直(vertical)拍攝的照片,其餘為斜影(oblique)或透視角度(perspective)照片。美國國家檔案館亦存有日軍在1942至1943年拍攝的香港航空照片,但由於資料散失,現時只餘下新界的兩卷照片,大約覆蓋后海灣到船灣、屯門至西貢半島一帶。
美軍在香港拍攝照片的原意是為了尋找目標,並為地面情報提供影像證據,以在空襲中準確擊中目標並減低不必要的傷亡。日軍拍攝航空照片的原因則可能是為了理解各區的空間以備將來的發展。這些照片雖然在當時有不同的用途,但對我們而言則是珍貴的歷史資料。首先,現時我們共找到十多批照片,分別在佔領期間的不同時間拍攝,最早為1943年7月,最遲則為1945年4月。這些照片為香港在此期間的空間轉變留下了具體的紀錄,彌補了文字敘述的不足。
雖然這些照片或許因為破壞與佔領而生,但它們卻無意中為我們保留了一些本來已消失的空間和建築物的影像。在香港淪陷前數年,市區(特別是九龍和港島北岸)出現了不少現代建築,它們大多呈流線形的設計,擁有獨特而簡潔的外形,在航空照片中亦可清晰辨認。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1941年完成,在1960年代初被拆卸,重建為今日重慶大廈的「重慶市場」(Chungking Arcade)。今日成為歷史建築的例如中環街市與灣仔街市,亦可在航空照中看見其洗練的身影。我們亦可見當時報紙提及,但戰後少有被人提起的日人建築,例如九龍城的街市、石屋(今石屋家園),九龍塘的「模範村」,以及近日因為發現埋藏了日本刀而再被提及的忠靈塔(前金馬倫大廈地基處)。此外,照片亦可見各地的陣地與隧道工程、長洲島的神風洞、臺拓農場(在大埔康樂園、軍地馬場、錦田機場、沙田日本人哥爾夫球場,以及粉嶺哥爾夫球場等地)的開墾,以及西貢道路等空間變動。
填補空間資訊 助歷史訪談
從航空照中,亦可見歷史建築的變遷及破壞。例如,我們得以在照片中看到日軍摧毁衙前圍一帶的村落,以及啟德濱、宋王臺等地以擴建啟德機場的過程。照片亦為部分戰時情况不明的建築提供線索。我們以往只知道中央書院(皇仁書院)的校舍在戰爭期間被破壞,但未知校舍是毁於香港戰役期間還是往後盟軍的轟炸。從航空照片可見,早於1943年7月校舍的屋頂已不存在,但仍可見外牆的大部分。至於1945年2月的照片則顯示外牆只剩下一面,其餘已被拆毁。書院後方的卅間(部分戰後重建的樓宇今日被活化)的情况亦相似。不少戰前建築在戰後被多次改建,或有新增的部分。由於戰時航空照片提供了從上而下的獨特角度,它們可讓研究者利用其他戰前(最早至1924年)和戰後(例如非常清晰的1963年)航空照片作比對,以在檔案不全的情况下辨別出建築物不同部分的興建時間。例如,我們現時可比較戰前與戰後的照片,了解被日本軍政當局大幅改建成日式的前港督府(今禮賓府)。
此外,以往不少口述或回憶紀錄其實包含了大量空間資訊,但研究者由於對歷史空間理解不足,或因為缺乏資料而未能將前人的回憶有效地置於具體的空間背景下討論,因而難以展開對遠近、大小、高低等空間觀念及感受的討論。筆者不止一次在聽以往的口述歷史訪問時,發現受訪者希望多談當時所處的空間,但訪問者確未有跟進而轉移了話題。筆者亦曾有機會與親歷其境者透過地圖交流,如前地政總署測繪處處長梁守肫先生,他曾撰文提及其經歷,並與航空照片證據相結合(《信報》「天圓地方」專欄,2023年11月14日)。此外,部分流傳已久的說法,卻因為航空照片的出現而得到具體證據,例如西營盤今日佐治五世公園位置的亂葬崗(實為臨時墳場),以及在空襲中逃過一劫的紅磡觀音廟。如將來從事口述訪問者更多使用例如航空照等更多圖像及空間數據,或許可以對訪問工作有所幫助。
數碼整合互動地圖 重構歷史空間
這些戰時照片更可利用數碼方法處理,成為應用更為廣泛的史料。近年,利用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GIS)進行歷史研究已頗為普遍,我們亦利用部分戰時航空照片完成「日據香港空間史互動地圖」。使用GIS使我們可以把各種史料(例如檔案、口述歷史等)以視像化的方式並列,並一定程度上重構歷史空間,使相關的討論得以更為具體。GIS亦可快速置換不同時期的航空照片與地圖,使研究者可以輕易作不同時期以至今日的比對。航空照片加上其他例如電話簿、物業登記等地理資訊,亦使我們可以具體看到香港不同族群和群體的空間分佈,並更為了解與之相關的多樣經歷。例如,居住在九龍塘與何文田一帶的葡籍群體,他們的戰爭與佔領經歷即與居住在西營盤的潘廣樑先生或官涌的梁守肫先生大為不同。
借助航空照片,我們可以發現香港各區在戰爭中的經歷不可一概而論,雖然部分軍政措施在各區均大致相同(例如憲兵部的高壓統治),但由於日本軍政當局對各區用途的規劃,盟軍空襲的猛烈程度,以及當地抗日與地下活動的多寡亦使各區的經歷及因此帶來的空間改變有所不同,亦可見文字敘述中未必提及的部分。戰時航空照片的發現,顯示日佔時期及香港史的研究中,即使官方檔案資料仍有等待發掘的地方,私人資料更急需更多有識之士參與蒐集和整理分享。隨着更多資料被發掘,我們不但可以重新審視日佔時期的歷史,發現並了解更多不同的歷史經歷,更可以探索戰前與戰後香港歷史的延續性及不同之處,將日佔時期置於香港歷史變遷的背景下討論。
文˙ 鄺智文
{ 美術 } 張欲琪
{ 編輯 } 王翠麗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