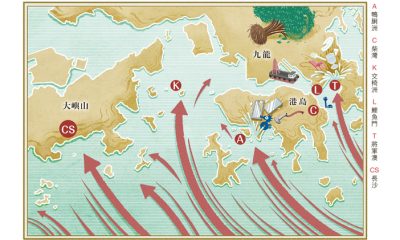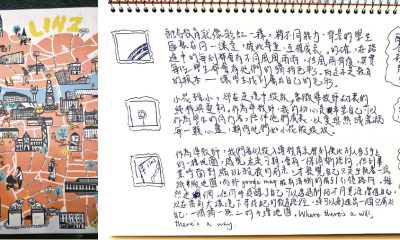副刊
周日話題:估得到個結局,估唔到個理由

【明報專訊】在樺加沙襲港之日,宣布「現屆政府維持暫緩實施垃圾收費」,環境局也許會解釋:9月29日開會,提早一星期發放文件好正常吖。然而畢竟是重要政策,本屆政府2022年第一份施政報告表明,「積極籌備最快明年(2023)實施的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如今政策煞車,施政報告不提、局長謝展寰在記者會兩次被問都不答,在打風之日才「官宣」是否適宜?大眾不笨,自有判斷。
1.唔講以為是財政司網誌
關於煞停的理由,文件引述民調「約七至八成受訪市民認為現階段不應該/不適合推行垃圾收費」,「物業管理、飲食及清潔業等……不希望政府急於實施垃圾收費」,而且「在全球貿易戰和地緣政治局勢日趨複雜的背景下,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和貿易中心正面臨多重挑戰」,政府要「避免政策對市民和商界帶來額外負擔」,因時制宜制定減廢策略。
萬料不到垃圾徵費會跟地緣政治沾上邊,唔講仲以為睇緊財爺網誌。老實說,由免費變收費,不論何時做民調,都肯定有很多市民反對的——甚至,對收費的抗拒正正是政策原意:令你扔垃圾要有成本、從而「利誘」你拿去回收,減少垃圾量。
又,如果民意反對、業界反對,政府就會無期暫緩一項政策,今年cut了2500元開學津貼,我身邊的家長朋友由預算案鬧到去施政報告,也剛好時值「全球貿易戰和地緣政治局勢日趨複雜下,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和貿易中心正面臨多重挑戰」,咁,會否undo唔cut?
由垃圾徵費條例2021年8月26日通過開始,官員必然深知這是不受歡迎的政策,今屆政府既然接過了任務,承諾「積極籌備實施」,那麼真正挑戰在於如何善用準備期把政策落地,引導民意明白這是長遠對環保有益的政策,減低阻力。然而,本屆政府的籌備工作起步很遲,每每「死線臨頭就delay」:
原定2023年底實施,同年7月謝展寰以「年底多節慶」為由,延至2024年4月實施;
臨實施前幾個月,加大宣傳,但民間質疑細節粗疏、難執行,官員解說也效果不彰,例如「如果你想不清楚,幾時都不清楚」、地拖棍可鋸開兩截棄置等等,可算是民意轉捩點;
2024年1月19日:宣布垃圾徵費延至8月1日,謝展寰當時指「有信心8月順利推行」;
2024年5月27日:政府宣布8月不推行,承諾2025年中到立法會交代;
2025年4月至7月:交代的日期再延;
2025年9月23日:宣布本屆政府繼續暫緩。
政府在2024年頭宣傳徵費期間,被揭出諸多執行漏洞後,似乎全無意志把方案改動到貼近香港實况,在暫緩的整整一年多,也沒有任何關於「實施徵費」的討論。「本屆不推」是早已寫在牆上的結局,寫得出來的理由是「全球貿易戰加地緣政治複雜」,沒寫出來的,恐怕是「準備不足,解說無效,也欠缺意志補救」。
2.比較基線不一致
文件裏有一些正面的訊息:
「本屆政府成功扭轉廢物棄置量長期上升的趨勢。
人均棄置量亦已由2021年的高位每人每日1.53公斤持續下降至2024年每人每日1.40公斤,三年間下跌約8.5%。
都市固體廢物的整體回收率亦正在上升。總回收量由2020年的低位約154萬公噸增加至2024年約202萬公噸,回收率由28%上升至34%。」
讀文件時有點好奇:為什麼「棄置量」是跟2021年比,「回收量/率」卻是跟2020年比?
以人均日均棄置量為例,
2021->2024,是1.53公斤降至1.4公斤,降幅8.5%;
2020->2024,是1.44公斤降至1.4公斤,降幅2.8%;
至於回收率,
2020->2024,是28%升至34%,升了6個百分點;
2021->2024,是31%升至34%,升了3個百分點。
基點不同,效果也不同,這文件的取材準則似是「邊條數靚就用邊個」,但就略嫌不統一了。
撇除以上瑕疵,近年回收意識的確提高了,每逢樓下開「綠在區區」站,很多街坊會拿廢物換禮品(我阿媽特別喜歡換米),這熱情會否因為明年「綠綠賞電子化」而冷卻?值得觀察。但「棄置量下降、回收率上升」,怎看都屬可喜趨勢。
3.徵費不在,要重繪藍圖嗎?
但若果我們把這幾年的趨勢,放在更長的時間軸,又會看到不同景象。
董建華年代廖秀冬局長,2005年發表《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提出「廢物收費」,並定下回收率目標:
「政府目標是在2009年提升到45%的回收率,並在2014年提升到50%。」
2024年現況,比當年提出的2014年目標,落後16個百分點。
梁振英年代黃錦星局長,2013年5月提出《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13-2022》,列出減廢目標:
「2017年或之前,都市固體廢物人均棄置量減少20%,從每日1.27公斤減少到1公斤或以下。
2022年或之前,進一步從1公斤減少到 0.8公斤或以下。」
實況是,2024年人均棄置量,比當年提出的2022年目標,仍超出0.6公斤。
林鄭月娥年代續任的黃錦星,2021年2月再提出《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其時垃圾徵費已提交立法會,新藍圖是假設有徵費後的中期目標:
「把都市固體廢物的人均棄置量逐步減少40至45%,同時把回收率提升至約55%」
以2020年人均棄置量1.44公斤計,減40%即要減到0.86公斤;
而55%這回收率,現况也遠遠未及。
這兩個目標謝展寰不會不清楚,因為當時,他是環境局副局長。
最新文件中,仍有個願景目標:「進一步將都市固體廢物棄置量降至每日9000公噸以下(現在是1萬公噸),便可望2035年達到『零廢堆填』」,然而垃圾徵費持續暫緩後,前朝訂下的人均棄置量、回收率等官方目標是否仍管用?抑或我們要重繪「沒有垃圾徵費」的新藍圖、新目標?在文件中未見詳細着墨。
4.胡蘿蔔能取代大棒嗎?
就算政府不擬更新藍圖,也有責任論證:擱置垃圾徵費,其他措施能補足這減廢誘因嗎?
文件提及「未來廢物管理的方向和措施」,包括「多用宣傳教育,改變市民行為」;「持續完善回收網絡」;「與行業協作,共同探索和推進務實可行的環保措施」及「善用市場力量發展環境基建,協助綠色轉型 」。
然而正如前述,這二十多年來政府的長遠減廢策略都是胡蘿蔔(賞)加大棒(罰),而大棒之中,最被寄予厚望的就是徵費,由廖秀冬年代明言:「我們必須為我們使用過和棄置的物品承擔責任」,到邱騰華:「最重要的是引入經濟誘因,以推動減廢及廢物回收」,再到黃錦星:「垃圾按量徵費屬推動減廢減碳的火車頭,推進其他配套及回收產業發展」,可見官員一直視垃圾徵費為重要工具。如今只用胡蘿蔔、不出大棒,政府要作科學及量化的評估:當「獎勵招數」已出得七七八八,減廢回收的成效是否已臨樽頸?沒有徵費這工具,是否很難突破?
尤其是過去幾年,「綠在區區」的人手、營運、禮品等支出,愈來愈多:
2020/21年度1.62億
2021/22年度2.26億
2022/23年度2.7億
2023/24年度3.13億
2024/25年度4.75億
2025/26年度(預算)5.07億
在最新文件中,政府強調「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提升服務」、「以更低成本擴大回收網絡」,財赤嚴重,加上失去徵費收入去抵消這筆開支,胡蘿蔔有可能「愈來愈奀」。
微觀個案,以我媽為例,她儲廢物去回收,最大動力是兌換「水晶晶米」;明年改為換超市分數,她興趣大減;本來若有垃圾徵費,她為了省錢會「揼少啲、慳多啲」;如今不徵費、又冇得換米,她已表明會「冇咁神心」。是的,若失驚無神問她「你願意主動減廢回收嗎?」她實答願意,然而內裏是細密的心理權衡,因此文件那句「超過九成受訪市民表示願意主動參與減廢回收」、「相較懲罰性的垃圾收費,市民更願意接受協助性和鼓勵性的減廢回收措施」,不一定等於胡蘿蔔能取代大棒。
沒想過同一篇文,會出現全球貿易戰、地緣政治局勢,和我阿媽。然而家家戶戶扔幾多垃圾、拿幾多去回收,本來就是尋常百姓家的事,但願政府有宏觀視角之餘,多由小市民角度思考政策,既有條文框架,也要想通落地執行,萬一撞了板,就誠實檢討,重訂目標,重新出發。
如果這橫跨廿年的垃圾徵費觸礁能換取官員汲取以上教訓,咁總算,唔係白費——雖然,已經好貴!明天記得問謝展寰,枉印的垃圾袋垃圾標籤和行政成本,花了納稅人幾多錢?這筆帳跟誰算?
文˙林妙茵
編輯˙黃永亮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