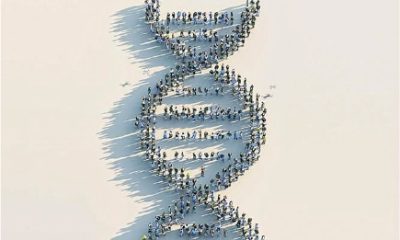副刊
未來城市:首試扶正救名木 棲身花槽將擴闊 復原靠養護也靠自己

【明報專訊】颱風樺加沙過境已逾一周,九龍公園的人行道邊仍暫放着高逾人頭的風後斷枝;園內依然寧靜,彷彿與一旁繁忙的尖沙嘴斷了訊號。眼下正值國慶長假,三三兩兩的旅客欲在粉紫色的噴泉旁取景,遭頭戴安全帽的工友勸返,只能在封鎖線外舉機拍到「邊角料」。九龍公園鬱鬱葱葱的樹木與噴泉如今已成為「打卡點」,許多遊人街坊未必叫得出樹名,卻記得某片樹蔭的四季輪廓、黃昏投下的影子,或是鬧市區小歇的氛圍感。城市的日常靠這種長年「看見——路過——再看見」的節律搭起來;一棵街坊樹倒下,地上多一塊窿,幾天後夷為平地,好似什麼都沒有發生,少一抹蔭,又惋惜難免。當前極端天氣漸頻,本次10號波後多了幾單案例,社區與政府不似以往急於清走樹障,在塌樹現場琢磨扶正與保留,為災後保樹留下討論的空間。或許,在聽天命之前,仍有不少可做的人事。
義工隊說
盡量保留枝幹 7吊點分散受力
記者於10月2日下午抵達九龍公園,主噴泉至樹木研習徑一帶仍全線封鎖,嘗試靠近施工範圍觀察,封鎖線內則一片忙碌。沿主噴泉的中軸線望去,約110年樹齡的大葉合歡在烈風過境後倒塌,於9月30日由「中國建築社區應急義工隊」(以下簡稱義工隊)搶救扶正。為防後續倒伏風險,目前現場團隊在樹周以沙袋壓穩根盤,並在樹幹腰身位設置鋼支架作加固。義工隊樹木專家Mick Tong表示,該樹肉眼可見的部分保存得尚算完好,泥膽並無裂痕散開,表面仍有很多健康的毛細根,有賴於倒塌初期適時保濕。老邁古樹經歷倒塌再扶正,等同人類進行重大手術,我們所能做的只有長期觀察健康狀况並盡量改善樹木身處的環境,長久存活,主要看樹木本身。
「早期局方四處諮詢,有反饋認為樹幹拉不直、難救返。」本身是立法會議員的中國建築國際集團副總裁、義工隊負責人陳恆鑌受訪時回憶,打風翌日獲文化體育及旅遊局請求協助,雖然初期局面不算樂觀,義工隊仍聯同土木部門、樹木專家與政府部門進行一輪詳細評估,「因為是古樹名木,全港約500棵,倒一棵就少一棵,市民同社會都希望盡量保留」。最終救援隊拍板「無論如何,都要試」,並按「盡量保留原貌」的原則設計救樹方案,而非像舊時般剪除枝幹。團隊認為,為了讓樹木日後有機會復原,應盡量保留枝幹;但同時也要剪去部分枝幹,減輕重量、保持平衡,確保吊運時安全。兩者之間要拿揑得宜,並不容易。
談及救援難度,陳恆鑌指出,現場所見的大葉合歡因年事已高,「樹體狀况麻麻地」,現場評估「裏面有蛀、樹窿」,以至任何受力都必須謹慎——古樹緊貼硬化路面與噴泉水池,重型機械不能貼身操作,只可把吊機停在約60米外發力,對一棵歷經風折的古樹而言「風險的確好大」。團隊先以單點發力試升,拉力至約20噸仍難以扶起,遂將力分散至7個吊點,以尼龍吊帶配保護墊包裹樹身。最終,古樹被穩妥送回原位,並加設臨時鋼支架作結構支撐。
至於受創如此嚴重的老樹,未來能否恢復如初,陳恆鑌表示尚難斷言:「畢竟這棵樹已有百年樹齡,狀况本身不是百分百健康,後續是否能重新穩定、長出新根,有待樹木辦與康文署等專業部門評估。」他補充,義工隊與工程公司已在盡量減低對樹健康影響的前提下,將其復位至「仍可生長」的姿態,未來的恢復不僅需要各方努力,也要靠這棵樹自己的努力。
民間觀察
「花盆」限制發展 倒樹成因不一
經過救援隊營救,九龍公園大葉合歡的命運似乎已到聽天命的階段,但在極端天氣造訪之前,仍有些許未盡的人事。
若將視線拉遠,過往的塌樹事件有留下一串尚未解決的記號。翻查過往塌樹的社會討論,記者在關注樹木保育與環境監察的民間組織「長春社」網站檢索到多篇對塌樹事件的紀錄與分析,發覺塌樹成因不一,有時無關風雨。2007年,同屬九龍公園、冠以「香港市區樹王」之名的榕樹約三分之一樹幹倒塌,長春社其時撰文分析政府護樹資源不足,未能充分掌握樹木健康,並促請盡快加強詳細檢查與補救。2022年,何文田巴富街一株鳳凰木則無徵兆倒塌、砸中校車。長春社梳理個案與10多年來對塌樹事件的紀錄,指出不少事件其實反映長期的結構性隱患:在受限空間生長的成熟大樹,基部或根部健康惡化,嚴重時僅受到些微外力,足以在風和日麗時倒伏。
長春社總監蘇國賢向記者解釋,與其餘塌樹狀况不同,颱風帶來破壞結構的極端外力:「就算樹木一點缺陷都沒有,面對足以超過承受力的外力,如很厲害的颱風,亦有可能倒塌或折斷。」年長樹木樹冠龐大,迎風面像帆,當外力大到某個臨界點,就會失守。「譬如颱風後見到很多種不同的樹同時間成片遭到破壞,其實就反映了應該是一時一地烈風極強,令不同的樹種都無法承受,造成較大規模的破壞。」
塌樹並不總是「集體現象」,蘇國賢補充另一類由localized(局部化)因素觸發倒樹現象:「有時整條街某個位置特別當風,又或某棵樹本身存在結構缺陷,會造成某一棵會倒塌或折斷,其餘樹仍完好的情况。」他舉例,部分屋邨個案可見樹根是整體脫落、暴露出來,「在地上一個四四方方的框,我們叫樹穴」。四四方方,倒塌後視覺直觀可見其中的非自然要素,由於樹穴限制,根系難以外展,加之有年份的樹冠碩大,較食風,最終在烈風下失守。換言之,烈風確實有機會打倒健壯的樹,但在城市環境中,樹的承受力與恢復力亦受長年生長環境與照料影響——根盤能否伸展、土壤體積與孔隙是否充足、修剪維持在不宜被烈風破壞結構等等,皆是要素。
那麼,這次九龍公園的大葉合歡是否也存在「結構受限」的因素?根據現場初期影像與報道,塌樹並非單純折斷或傾斜,而是泥膽連同花盆內土體出現側滑,報道描述常用「吹倒」「吹歪」「不敵強風」「連根拔起」等字眼,固然強調風是最強的致命一擊,但之前多年的「積弱」也需要被謹慎考慮。花槽令根盤受限、根系發展不充分則影響抗風、穩定性,如此生長30餘年,颱風有概率將不太理想的生長狀况推上臨界,觸發倒伏。
蘇國賢留意九龍公園這株大葉合歡已有逾10年,他指,該樹長期被圍圈在約1米高、2米直徑的圓形花槽內,但本來應該是地植,「80年代末(九龍公園)由軍營再度修繕為公園時,在樹幹周邊砌磚、築石屎花槽,形成今時狀况」。多年來他見到樹根被擠迫着向外生長,又因地磚無法獲取水分,長此以往,根系有概率枯死、腐爛,「我已經反映和憂慮了10幾年,最後(倒塌)真的發生了」。不過,他肯定今次處理方向已不同於過往「最簡單、最快、最便宜」的一砍了之:「這次無論在愛民邨還是九龍公園,政府沒有立刻移除,而是先想辦法救樹,這個決定本身令人鼓舞。」他補充,關鍵在後續——日常監測、土壤與樹勢的養護是否持續投放資源;「若做到,相信救到樹的機會是有的。」
康文署回覆本報表示,在審視古樹的健康及結構狀况並扶正後,以鋼架加設穩固,現正進行最後階段擴闊花槽的工程,由於樹木大部分根部已嚴重受損,其復原進度仍有待觀察。署方會密切留意樹木的生長情况及復原進度,採取合適的護養方案,盡力保留古樹。
幸運vs.常態
扶正救樹須考慮場地、時間、技術
蘇國賢從應急處理角度指出,「如果一棵樹倒在極繁忙路段,通常就『玩完』——要盡快清場開路;就算扶起,日後也可能再倒塌,過往很少有空間思考是否有其他方案」。今次10號風球下,愛民邨與九龍公園2單個案不再只求最快清理,而是在可行與安全前提下嘗試保留,關鍵在於兩處不屬繁忙區域,可暫時圍封,毋須即時清場,爭取了更多時間,能先確保公眾安全,在風險可控下評估與施作。「都覺得可能在想法上有所改變,或許也與社區的聲音有關,可能真的大家思想上都有所改變,這個是好的方向。」九龍公園大葉合歡得以扶正,確有「運氣成分」;未必能以部門、管理者的決策一概而論。只有在場地安全、時間與技術可行性具備時,「救或不救、如何施救」才真正有討論空間。
同時,中建公司的救援隊為義工性質,救援隊在訪問時表示已經在災後連續數日投入人力,現場施工、收工後開會交流,不斷磋商擬定救樹方案。除了救樹,他們還協助黃竹洋村清理道路、修復斷電區域等,補位了政府部門在短時間內難以兼顧的緊急需求。若應急資源有限、時間緊迫,更難在短時間內想到更好的方案,第一時間要清理路面,而無餘力救樹、再投入做好日後養護。現在,樹暫時保下來了,但這是否能成為常態,仍取決於制度與資源是否願意為一棵樹保留一點餘地。
籲改善古樹原生種植空間
一次幸運的救援,未必能成常態。下一棵倒下的樹未必有同樣的等待空間?
問及災後塌樹的分類與處置經驗,陳恆鑌指出,風後倒樹可大致分為3類:其一為路邊常見的速生易倒樹種,例如銀合歡。「在路邊生長的銀合歡很多,風後清理時常見其垮塌」,他補充銀合歡屬入侵種,生長快、競爭性強、排他性高,不僅脆弱易倒,也對生態造成壓力,原則上應被逐步控制與移除。其二為本地常見的短壽種,如台灣相思。進入生命後段時木質腐朽,難以承重,終致傾倒。「這類樹多數已經無法挽救」,倒塌或是遲早之事。其三則為非計劃植栽、偶然落地生根的個體,例如颱風韋帕期間倒塌的小瀝源邨印度榕,樹齡40餘年,卻非來自規劃種植,根系多半浮淺,加上生長於石屎覆蓋的環境,缺乏紮實根基。「這類樹在森林裏或許能自立,但在城市裏風險太高,義工隊最終判定不宜保留,經3日處理完塌樹現場。」
這些分類反映出一個結構性現實:城市之樹的存亡,除去極端天氣的風勢,品種選擇、根域規劃、養護制度與空間管理等因素同樣需要被考慮。參與義工隊的樹藝專家、安盛園藝有限公司董事Mick Tong表示,救援團隊已向有關方面建議給予本古樹更多生長空間,康文署擴闊花槽的後續行動,料屬其中一環。「因為歷史遺留的問題以及樹藝科學當時並未在港普及,香港以往大部分栽種樹木的環境都未能盡如理想,希望有關當局以後可下放更多資源着手研究,將有條件能改善原生種植空間甚或能移植的古樹羅列並制定可行方案,同時,新栽種的樹木能繼續秉持局方「right tree, right place」 的原則。」若能從塌樹迹象回溯遺存的改善方向,進一步促成前瞻性措施,例如在選樹時同步考慮樹種特性、預留根盤空間便於日後養護,在城市空間中安置適合的樹種、修正歷史遺留錯配,那麼「致命一擊」或許就不再是命中註定,而是一次可以被管理的風險。烈風是天命,天命難測時,人事還可做的更進一步、更細一點。
【風來樹倒篇】
文˙ 于惟嶼
{ 圖 } 鄧宗弘、賴俊傑
{ 美術 } 朱勁培
{ 編輯 } 梁曉菲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