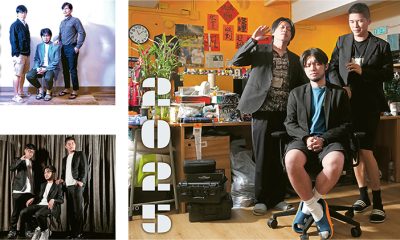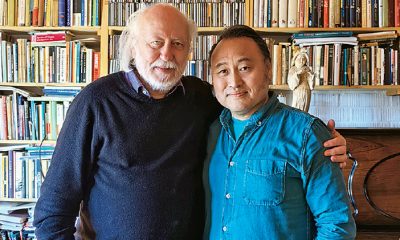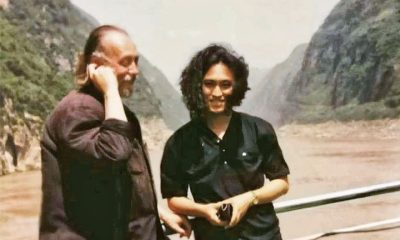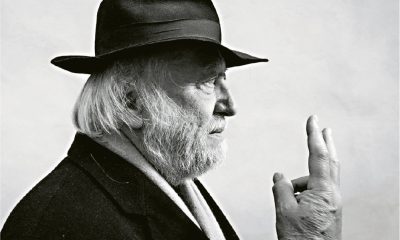副刊
周日話題:《東方三俠》:曾幾何時的港產獵魔女團?

【明報專訊】Netflix動畫KPop Demon Hunters(下稱 KPDH)風靡全球,不僅成為平台史上觀看次數最高的電影,原聲大碟更獲白金銷量,主打歌Golden蟬聯Billboard冠軍八周,堪稱今夏奇迹。三位身懷絕技、平日大隱隱於市的女主角,暗地裏行俠仗義守護人間,不禁令人想起1993年杜琪峯執導,梅艷芳、楊紫瓊與張曼玉主演的《東方三俠》。
KPDH開場不久即以節奏明快的How It’s Done配合一場炫目的打鬥,迅速建立Huntr/x三位女團成員Rumi、Mira與Zoey的鮮明性格。《東方三俠》亦不遑多讓,片頭全黑襯以〈莫問一生〉雄渾歌聲,將「樂壇大姐大」的氣場延伸到戲中的女俠英姿。兩部以女性為核心的都市奇幻故事,同樣糅合東方神話、武術、流行音樂與現代都會美學,卻從開頭走上不同的分岔路,彷彿交代了香港與韓國兩大潮流文化三十年間的此起彼落。
身分掙扎與自我認同
KPDH由古代朝鮮作序幕,轉戰現代首爾。從街頭、體育場、古城牆,到杯麵、紫菜包飯等食物,以至女團的玉佩與武器、男團的韓服與斗笠,在在展示韓國的文化傳統。然而,故事核心始於個人身分與成長掙扎——勇於面對失敗、偏見的自我救贖,儼然是一套穿上韓服外衣內核卻是典型「up, up, up with our voices」的American Dream。Rumi半人半魔的模糊身分,大致也是幕後主創與至配音和主唱的韓裔美籍/加籍班底,面對族裔與文化間夾縫成長的折射。至於韓劇常見的復仇與家族糾葛,在老少咸宜的動畫載具中,都給Soda Pop般的輕巧甜蜜中稀釋,只留下《社內相親》般的碰肩邂逅,讓全球觀眾在輕快節奏中樂而忘返。
相比之下,《東方三俠》的基調顯得沉鬱凝重。嬰兒連環失蹤,背後是太監(任世官)主導的皇朝復辟陰謀,象徵一座城市的existential crisis。面對大限來臨,市民沒有玩樂嬉戲的餘閒。後現代三女劍俠面對着諸多「情和情和情的關」,時刻都要思前想後。東東(梅艷芳)縱使武功高強,卻要隱藏實力當起英明幹探(劉松仁)背後的賢內助,陳三/青青(楊紫瓊)本是東東師妹,因學藝未精而被棄師門、繼而給太監操控潛藏在科學家(白石千)身邊竊取隱形技術,一樣要扮演小鳥伊人。惟有賞金獵人陳七(張曼玉)能夠瀟灑地獨來獨往。
三十年前後,兩代女中豪傑同樣掙扎於雙重身分,東方三俠「等了多年這角色/做你的女人」,面對壓力時「你我卻須要/在人前被仰望」;獵魔女團雖然一樣要「live two lives, tried to play both sides」,最後卻能「let the past be the past’ till it’s weightless」而自我釋放。從不知名的海邊城市,到二次元的首爾,歌聲中盪迴的正是偶像與凡人面對身分抉擇的不同取態。
傳統文化的呈現與再造
《東方三俠》的陰暗壓抑與KPDH的明亮奔放,不僅體現在角色命運,也反映各自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同時側現港韓兩地當時的社會脈絡。
《東方三俠》裏的傳統符碼,從「中國唔可以無皇帝」的口號,到陰森詭異的地下世界、以血滴子為武器的武僧陳九(黃秋生),反映了當時人們對傳統的疏離與惡懼。香港自開埠以來長期受西方影響,至1990年代早已以現代化自豪:法治、廉潔、高效率的社會,影視作品不時都以「urban cool」形象與傳統中國社會作出區隔。1980年代以降,港產片逐漸由古裝武俠或民初功夫片種,轉向現代警匪片或英雄片為主,如《英雄本色》、《龍虎風雲》、《無間道》,又或杜琪峯後來拍攝的《非常突然》、《鎗火》、《PTU》,甚至《黑社會》等,無論黑白兩道都以專業團隊形象,穿梭於大都會之中。《東方三俠》於1993年上映,九七大限將至,面對可能的秩序和法規崩塌,宛如皇朝復辟的陰霾驅之不散:一年前徐克執導的《妖獸都市》,妖魔首領(仲代達矢)盤踞中銀大廈頂層發放「妖閉空間」,使全港時間倒流,同樣是一整代人對未來失控的恐懼投射。
相對之下,KPDH的文化姿態明快而自信,由韓裔加籍導演Maggie Kang與北美團隊創作,將韓國元素自然融入全球敘事之中——從角色造型、場景建築到歌詞意象,無不滲入韓國民族特色。動畫以3D技術結合二次元動漫風格,塑造出既搞笑又剽悍的「太極虎」形象,吸引全球不同文化、性別、年齡的觀眾群。這種文化自信,與韓國社會在經歷殖民統治、戰爭與獨裁後的民主化進程密不可分。全民對歷史的共識與民族自尊,使文化創作敢於直視傳統並再造。韓裔加籍學者Kyong Yoon在《離散韓流》(Diasporic Hallyu)指出,韓流不只是一種族裔媒體,更是全球性的媒體,讓離散在外的族群藉此理解自身身分,無須時刻依附於西方主導的文化框架。這種學術觀點,正好透過同樣是加籍韓裔導演的作品,透過音樂和影像發揚光大。
垂直整合模式的前世今生
兩星期之前,Huntr/x三位真人主唱Ejae、Audrey Nuna和Rei Ami首度現場表演Golden,社交媒體瞬間洗版。美國粉絲紛紛感嘆Ejae擔當SM Entertainment練習生12年,先後與少女時代、Super Junior、f(x) 等二代韓團同期受訓卻無法出道,轉戰作曲多年始憑KPDH一鳴驚人。Huntr/x don’t miss熱爆全球,韓風究竟how it’s done?曾風靡亞洲的港式流行文化是否錯過什麼?
韓流三大支柱K-Pop、K-Drama、K-Film三十年來受惠於國家產業政策,同時以垂直整合的內容生產模式大盛。韓國作為典型的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政府一直主導經濟發展方向。1961年朴正熙軍事政變上台,旋以「富國強兵」為目標,推行多個五年計劃,大力發展重工業並與財閥合作,使韓國迅速躋身亞洲四小龍之一。然而過度干預亦埋下企業效率欠佳和債務過分擴張的禍端。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國家幾近破產邊緣。1998年金大中當選總統後積極推動改革,將政策轉向資訊科技與文化創意產業,同年向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KOCCA)注資5000萬美元,直接支援創意製作與出口,年度預算如今已逾四億美元。業界方面,SM、YG、JYP三大音樂品牌於1995至1997年間相繼成立,紛紛展開垂直整合的生產線——從練習生選拔、軍事式培訓、錄音製作、發行宣傳等,每年創造出逾萬首歌曲,正是往昔韓國重工業流水作業的變奏。韓裔美籍學者Solee Shin分析,K-Pop的垂直整合模式,有利統一歌曲及表演風格並提升品牌識別,同時與各國機構媒體合作,擴大發行網絡,成功創造市場主導地位。SM 旗下「元祖男團」H.O.T. 與其歌曲Candy,正是KPDH導演創造戲中Saja Boy外形與歌曲Soda Pop的靈感。
其實這種垂直整合的內容生產模式,早於 1950至1960年代便在香港出現。當時國泰、光藝、邵氏等電影公司先後在港設立片廠,年產合共逾300部作品,媲美荷李活、印度與日本。最具代表性的邵氏兄弟公司,自1958年於清水灣興建片場,十多個攝影棚24小時運作,自家培訓演員、編寫劇本、混音冲印,統統不假外求,成為亞洲最大的電影製造基地。邵氏本身已在南洋擁有龐大發行與放映網絡,遷至香港後與日本、韓國等片廠緊密合作,形成跨國垂直體系,輻射整個東南亞。在未有互聯網的年代,或影帶影碟租賃前,戲院屏幕是集體消費娛樂內容的主要渠道,那時候邵氏的覆蓋和產量不下今日串流平台,幾乎每星期都有新片上畫。
湊巧的是,如今以KPDH走紅的Ejae,其外公申榮均正是初代韓國「韓流」代表——1950至1960年代,韓國名導申相玉創辦的申氏公司旗下首席男星。1962年他憑《燕山君》(正是《暴君的廚師》那位暴君),奪得韓國首屆大鐘獎最佳男演員,並兩度榮膺亞洲影展影帝。同年在韓國舉行的亞洲影展,邵逸夫與申相玉一見如故,雙方達成合拍協議,推出4部伊士曼彩色古裝鉅製,其中一部便是傳奇女星林黛主演的《妲己》,申榮均再次飾演暴君——紂王。冷戰高峰時期,邵逸夫把握香港的特殊地緣政治地位,利用各國的製作技術與人力資源,往往將一片三拍,以供本港、東南亞和歐美市場上映,以迎合不同電檢尺度和觀眾口味,其文化適應能力尤勝今日串流影片的多語言配音。
今日韓流大盛,國家支持不可或缺,而申氏公司正是電影學者李尚埈所稱「發展型國家製片廠」的始祖。申相玉憑藉與朴正熙的關係,獲得不少政策支持而成為韓國影業翹楚。相比之下,以自由市場見稱的香港,官方並無直接資助影業。然而邵逸夫素來長袖善舞,積極與星、港兩地殖民政府維持良好關係,甚至王室成員來港亦每多造訪影城。根據英國官方檔案,港督葛量洪在任期間多次與新加坡總督游說支持香港電影工業,確保港產電影在冷戰夾縫中意識形態的領先地位。邵逸夫將生產基地由馬來西亞遷至香港之決定,亦正是葛量洪任內提出。邵氏雖無申氏般直接受益於國家發展政策,然而一如《香港電影與新加坡》所述「在冷戰的高峰期,香港影業於商業運作背後,政治力量在幕後的干預/參與是不容忽視的」。
踏入1980年代,邵氏電影固步自封,依然沉醉重塑「『去國式』的中國歷史面貌與想像」,票房與產量俱每况愈下。邵逸夫最終轉換跑道,將垂直整合模式移植至無綫電視,影城改建為「電視城」,儘管多年來流水作業的公式化創作每多為人詬病,穩定的產量與收益為從業員提供保障,也奠定了香港影視的制度基礎。1980至1990年代港產片黃金盛世,邵氏已幾近消失,但其培訓體系與製作技藝深植業界。譬如《東方三俠》導演杜琪峯出身自無綫藝訓班,早已習慣片場內狹窄空間的調度,擅用機位和剪接來彌補資金和環境不足。梅艷芳從無綫與子公司華星合作之新秀歌唱大賽出道,及後透過劇集主題曲的洗腦式播放而紅遍全港,正是垂直整合生產模式的表表者。回望至今在韓國歷久不衰的《英雄本色》,豪哥、Mark 哥、杰仔(狄龍、周潤發、張國榮)的銀幕形象,以至吳宇森師承名導演張徹的暴力美學,都是繼承了邵氏垂直整合體系的產業基礎。香港雖非developmental state,然而流行文化曾盛極一時,甚至滋養了韓流的成長,實有賴這種微妙的公私合作模式。
遲遲年月回望過去,1997年成為香港與韓國流行文化分道揚鑣的轉捩點。香港流行文化走到盛世的頂峰,雖然歌影巨星依然紅遍亞洲,但在知識產權管理、周邊行銷、經營偶像社群與工業化製作上逐漸給擅長國家發展模式的韓國後來居上。金融風暴之後的蕭條,本地財團也再無豐厚資源深耕細作式運作,加上種種有形無形的創作限制,港產流行文化在製作規模和視野已難望韓流之項背。如今KPDH,以密集不斷的笑料,結合愛情親情友情於一身的情節,輔以目不暇及的動作打鬥和洗腦悅耳的流行歌曲,老影迷不禁覺得似曾相識,那不就是港產片從前的拿手好戲嗎?然而,KPDH早已超越一國潮流,而是跨國資本與全球頂級創作班底的合力結晶。回望《東方三俠》,那一頁「動地驚天放聲笑傲」的傳奇,總算是Canton-Pop浪潮一頁「滄桑裏自有浪漫」的美好回憶。
文˙奇夫
編輯˙黃永亮
fb﹕http://www.facebook.com/SundayMing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