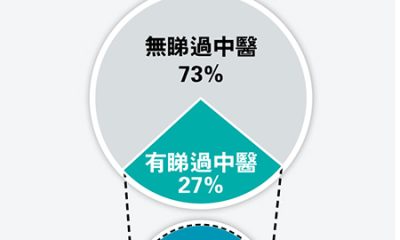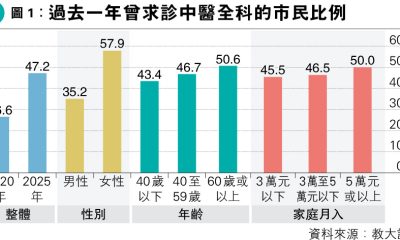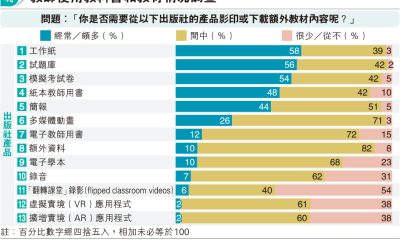觀點
趙永佳、梁雅文:誰的成功——Band 1名校中的「平凡學生」

【明報文章】自上世紀70年代起,香港的學校「Banding」分班制度誕生,最初不過是行政上的方便,卻漸漸成為社會階層的隱形標籤。Band 1被譽為「精英搖籃」,彷彿踏入其中便握有「成功」門票;Band 3則被貼上「墮落區」的烙印。然而在被光環籠罩的名校裏,是否每個學生都能如願踏上所謂的「成功之路」?
事實上,於Band 1校園裏,隱藏着一群「平凡學生」——他們未能藉DSE(中學文憑試)直通大學,只能走副學士、基礎文憑的「繞路」,努力重返正軌。根據數據,每年約5萬人報考DSE,僅約1.5萬人透過JUPAS(大學聯招)躋身「八大」,另有約5000人則經副學士或高級文憑,以「高年級生」身分重返大學。這些人不是失敗者,他們才是整個體系裏真正的「中位數」。
本文講述3名來自Band 1名校,成績未必出眾,卻依然努力不懈的學生:Jessica、Noah與Johnny。他們的故事如同一面鏡,映照出教育的本質,令我們不禁反思——到底教育之目的,是否只是為了「出狀元」?
「中學係一場我搞唔清楚規則嘅讀書遊戲」
小學時期的Jessica成績頂尖、字寫得靚、默書一字不漏,雖出身基層家庭,卻是老師眼中頂尖的「乖學生」。
「以前寫字練習好流行penmanship(英文書法)嘛,每當媽媽覺得我隻字唔靚,就會擦晒叫我重寫。」在媽媽嚴格督促下,她順利考入油尖旺一間傳統Band 1中學。本來暗地期望小學的「卓越」能延續到中學,但她很快發現現實不似預期。
以往Jessica只要早兩日努力背默,便能夠輕易取得好成績。「但去到中學,你會發現愈來愈多題目要你組織邏輯,或者需要你去思考」,她說。對於中英文作文,總是無法於時限內完成,數理科又完全不懂如何做,她直指「搞唔掂」。
面對成績轉變,她不是一下子放棄,反而頻繁上試卷操練補底班,亦主動詢問老師,惟收效甚微。「其實我覺得未必有用,因為你多做幾次都好,你冇嗰個技巧,都唔會變有」,她苦笑着說。
最令自己徒勞無功的感覺急劇浮現的,是老師無心的一句:「我真係唔明你到底係唔明咩。」面對老師眉頭一皺,Jessica對自己的能力充滿懷疑——難道自己真的是「教極都唔識」?
曾經最熱愛的自己,後來選擇「躺平」,「都係想補救,但可能會覺得太遲,補救唔到乜」。
Jessica無力感的內化,源於無法挽救「繪出成功故事」的機會。她曾以為只要努力,就能夠由基層躍升。可惜,她缺乏的從來不是努力,而是其他中產學生自小受過的「精心培養」(concerted cultivation):參加課外活動、擅長表達、具批判思維、熟悉制度——這些真正能夠於教育和社會體系裏取得優勢的「方程式」,卻從無人教過她。
「中學係一個放棄自己嘅地方」
Noah的故事,是另一種無聲的放棄。與Jessica相似,小學時的他有着「冠軍相」:幾乎年年當班長,是人人眼中的品學兼優模範生。儘管家境清貧,Noah順利升入深水埗一所Band 1中學。「即係升中嗰一刻,我已經覺得自己升咗入大學㗎啦。只不過冇諗到後面有咁多嘢發生」,他感慨道。
然而中二下學期,一場皮膚病爆發,改變了一切——臉上紅疹令朋友避而遠之,而本應守護他的老師與社工,卻只有「走過場」的隨便問候。那時的Noah,未察覺自己情緒已悄然崩潰。
「你會不會說學校重視同學的心理健康呢?」筆者問。Noah答:「唔重視,絕對。」
Noah回憶,學校唯一關心的是紀律與成績。學生在早會中暑,無人理會;訓導老師甚至強迫學生當眾除褲,只為檢查校褲牌子。學生的聲音,在這裏被視為笑話,非尖子生更是被忽視。這種情况,在Noah高中誤選兩科不適合自己的理科之後,更加嚴重。
物理老師從他考低分開始,就似乎放棄了他。課堂不講解公式背後的原理,課後問問題也被敷衍回應,「佢又好『hea』(敷衍),問佢問題都唔答,就令我覺得真係填鴨式教育嘅感覺囉」,Noah無奈地說。
知道自己無法達到大學最低門檻「33222」後,他選擇放棄,「反正讀嚟都冇用。」Noah並非一開始就覺得自己是「冇得救」,相反,是Band 1學校無形的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把成績和紀律當作衡量一切的標準,將他慢慢推向邊緣,陷入「我唔夠好」的內化與服從。事實上,他從不是「唔叻」,只是這套遊戲規則不適合他。
「中學係一場文化與語言嘅雙重迷宮」
Johnny的經歷,則是一場歷時6年的語言與階級夾擊。他的雙親出身草根,深信「傳統名校是成功溫牀」。聽聞友人兒子在油尖旺一所直資Band 1名校的成功後,他們雀躍地帶着小學成績不錯的Johnny參加該校入學面試。順利入讀的Johnny,完全不知自己即將踏進文化與語言的雙重迷宮。
該學校全英語授課、外籍老師眾多,對家境富裕的學生來說或許輕鬆,惟Johnny自小接觸的英語僅限課本內。本身英文底子不夠用時,他便成為課室裏唯一的「局外人」。「課堂英文我大概聽得明五成,但我仲消化緊上一句講咩,下一句已經跟唔到」,他坦言。
老師雖頻繁開設補底班,想拯救這個「學渣」,Johnny卻明白語言才是一切學業困難的根源:「當你英文唔得嗰陣,咁就所有嘢都唔得㗎啦。」學校的支援、配套,對他來說根本無法奏效。
中三時,他更因為無法跟上課堂,選擇「擺爛」,化學課一開始便趴在枱面睡覺。面對老師不悅,他卻不以為意。「因為真係聽唔明呀嘛,」他輕鬆地說。
語言之外,生活方式差異更是他難以跨越的高牆。當同學們談論英美加的旅行經歷、送出正版球衣作為手信時,他只能夠帶着一盒朱古力,感到自己彷彿身處「不同世界」。畢業之後,這種距離感愈加明顯:昔日同窗有人成為大提琴手、有人出外讀機師訓練課程;而他即使中六嘗試「搏盡無悔」、發憤圖強,DSE分數卻仍不足20分,只能走副學士再升大學的「繞路」。
Johnny表面假裝不在乎,惟內心對自己在校內與制度、語言的糾結深感困惑——「我真係咁渣?」他從未向友人吐露這份心境,因為他深知他們「唔會明」。他當時未曾意識到,自己並非沒有能力,而是名校制度可能只是為少數有能力的學生設計,而未能為「平凡學生」的需要設想。
失語青春的三重奏
本港Band 1學校出產了無數社會精英,自然有它的價值,也不會有人認為所有名校都是鐵板一塊,我們碰到的可能只是個別例子。然而,可嘆的是Jessica、Noah、Johnny 3人,背景不同,經歷各異,卻在同一舞台——Band 1學校裏,共同經歷着掙扎的旋律。他們既非最差的學生,也非最懶散的旁觀者,只是不符那套刻板定義中的「成功者」輪廓。
在香港,「成功」依舊被簡化成一條單行道:讀書、考大學、找份好工。然而這樣的單一標準,猶如一道高牆,將許多學生擋於門外。教育制度自詡公平,卻忽略了每個起點的迥異與不平等。
他們的故事,是對名校光環下「成功」迷途的低語與反思。或許該暫停片刻,輕聲問一句:「成功,是否只能有一種模樣?」
作者趙永佳是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與政策研究學系講座教授,梁雅文是前研究助理
(本網發表的時事文章若提出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趙永佳、梁雅文]